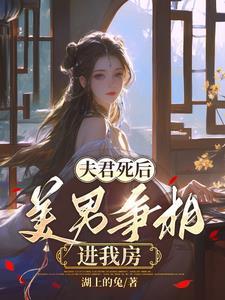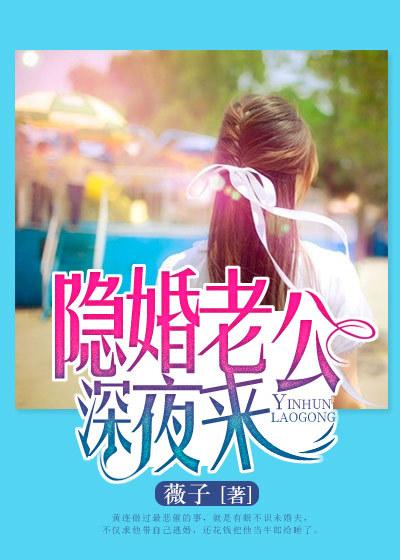紫夜小说>大明镇海王 最新章节 无弹窗 > 第19章 第十九章(第4页)
第19章 第十九章(第4页)
李武目光深沉地望着张刘氏,说道:“您稍等片刻。”
说完,李武起身走向院中唤张玉清。
张玉清起初并不知何事需要她出面,自打长子撑起门户后,她早已习惯依从长子的意见。
况且她清楚自己的性格,主意常摇摆不定,简单来说就是耳根子软。
然而听了李武几句提醒之后,她顿时来了精神,带着审视的眼神朝中堂走去,毕竟她家现今已非昔日可比。
就在同一时刻,中堂里的张刘氏正默念着李武家的事情,她环视四周,心中渐渐生出一种无力感。
这座宅院的气派,让她家望尘莫及。
张刘氏用力攥紧双手,暗自鼓劲,无论如何都要试试,毕竟自己的儿子如此钟情于对方。
不久,李武与张玉清来到中堂。
自父亲去世后,李武便成了家主。
家中事务,他通常不用回避。
他隐约猜到张刘氏此行是为了谈二贤的婚事,早已有所准备。
在彼此客套几句之后,便静静等待张刘氏切入正题。
张刘氏面带犹豫之色,或许是反复权衡两家的家境后感到为难,又或许觉得自己提亲这件事难以启齿。
然而,经过一番挣扎,她还是硬着头皮开了口。
“本来应该请媒人登门的,但我仔细考虑后认为,亲自前来更为真诚,也能说得更明白些。”
她停顿片刻,转向张玉清问道:“不知道令嫒是否已有婚约?”
张玉清微微一愣,这是她头一回见到对方的母亲亲自登门,难免觉得有些失礼,但她依然保持礼貌,微笑着答道:“尚未定下亲事。”
张刘氏心头一宽,这总算是个好消息。
她深知儿子张武对那个姑娘的倾慕,作为母亲岂会不知?多次看到儿子唉声叹气,她也不免忧心忡忡。
可这样下去终究不是办法,做母亲的总想成全孩子,即便她也知道两家条件存在差距,但还是忍不住劝儿子几次让媒人去提亲。
只是,不知为何,儿子每次都是摇头拒绝。
渐渐地,张刘氏开始怀疑是不是李武家的要求过高,儿子担心家里负担不起?
随着时间推移,她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但她不愿因金钱问题让儿子后悔终生,所以今天终于按捺不住,主动上门了。
至于为何不找媒人,她害怕媒人提及自家状况后被直接拒绝,倒不如自己亲自来,还能表达诚意。
张刘氏从手腕上摘下一只祖传玉镯放在桌上,深情地望了一眼,又毅然将目光投向张玉清。
“这是我家族传承下来的,到我这里已传了六代,我愿以此物求娶令嫒。”
说到这里,张刘氏稍作停顿,继续说道:“我家的情况,李百户想必是了解的,地处乡野,虽然儿子有些出息,略有积蓄,但确实比不上你们家的条件优越。”
即便家中再艰难,我也绝不推辞。
回去就着手准备一切事宜,届时必定派遣媒人正式登门提亲。
只求贵府能够答应这桩婚事。
我与他父亲年纪虽长,却依旧健在,还能操持家务。
我们愿意倾尽全力支持这对新人,只要令媛肯嫁入我家,我定会视如己出,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张刘氏言辞恳切,句句发自肺腑。
天下或许只有父母才会为儿女做到如此地步。
然而张玉清心中隐隐不悦,明知对方条件不佳还要提亲,虽心存善意,但涉及女儿婚姻时,难免有些强硬。
张刘氏转向李武道:“犬子乃你在军中的属下,你应该知道张武是个踏实肯干、老实本分的人,绝不会辜负令妹。”
此言一出,张玉清有所动摇,姐夫与小舅子这样的关系确实可靠,关键时刻往往能救命。
张玉清询问李武:“你说的是那个送来桑葚的小伙子?”
李武点头默认。
张玉清回忆起那健壮的年轻人,一时拿不定主意,似乎为了儿子可以适当妥协。
只是她想到二贤多年来勤勉坚韧,若将女儿嫁得不好,总觉得愧对,甚至悲从中来,几欲落泪。
然而就在此时,张武满头大汗地闯进屋内,梁方在后追赶试图阻止。
在场众人皆是一惊。
李武最先反应过来,挥手示意梁方退下。
张武对母亲抱怨道:“娘,您这是做什么?”
张刘氏瞪了儿子一眼道:“你喜欢人家姑娘,可你拙于言辞,纵使真心也可能引发误会,所以我才替你试试,就算不成,也免得日后后悔。”
说完,她又看向李武说:“莫怪我莽撞前来,听小儿多次提及你的事,知你家教良好,今日特来诚心拜访。”
此话让张武更加焦急懊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