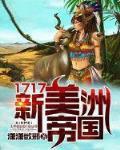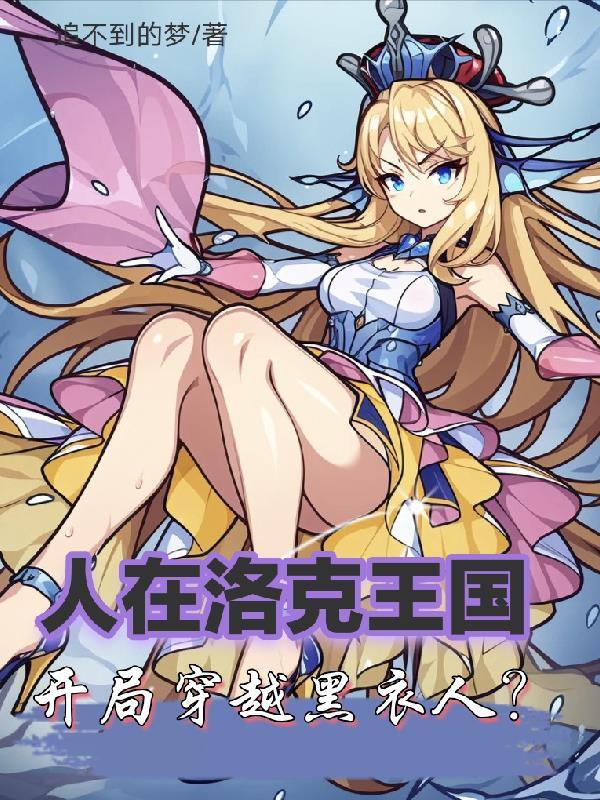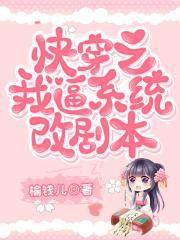紫夜小说>带我去远方综艺免费观看 > 第656章 抽卡小分队(第4页)
第656章 抽卡小分队(第4页)
期间又闹出了些笑话,比如当NBC电视台的记者将镜头对准街边的某座帐篷时,就发现帐篷正发出某种规律性的抖动。
正在记者疑惑之时,帐篷内又隐隐的传来了一股竭力压抑的呻吟。
“侯磊谢!”
记者不由得曝出了一句粗口,尴尬的把头扭开。
随着尼德兰德剧院门前的排队现象越来越突出,剧院开始担心这些热情的观众会把41街原本就不太良好的环境搞得更脏、更乱。
于是就将优惠票的售卖改为了抽签,观众们只需在白天到剧院售票处登记,在卡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把卡片交给工作人员。
等到每天晚上《父亲》开演前一个半小时,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就会在一顶帽子里抓取当天的卡片,通过扩音器宣布那些拿到票的幸运儿。
这项举措一出,立刻瓦解了剧院门口的“睡袋大队”
。
但却并没有改编《父亲》公演的火热势头,“睡袋大队”
没了,“抽卡小分队”
又来了。
每天晚上6点,尼德兰德剧院门口人声鼎沸,比演出入场时都热闹。
抽到票的人欢呼雀跃,没抽到的人怨声连连。
就这样,《父亲》在尼德兰德剧院公演两周时间,名声响彻百老汇,调动了整个纽约市的话剧热潮。
而火热的市场也为尼德兰德公司带来的丰厚的回报,公演仅仅两周时间,《父亲》的累计票房就达到了600万美元,顺利收回了全部投资,堪称神速。
这也代表着,未来《父亲》的每一场演出在刨除了剧院的运营成本、剧组的人工支出后,所获得的都是利润。
在乔治跟林朝阳分享这个好消息时,他已经回到了燕京。
“看来当初没有向你们收取高额版权费是正确的选择。”
林朝阳心情愉悦的说道。
当初在跟尼德兰德公司协商版权费用时,林朝阳并没有提出苛刻的要求,只是拿了象征性的1万美元的版权费,转而在版税分成上提高了一些要求。
百老汇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整个制作团队的收入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版税收入和利润分成。
版税收入跟利润无关,不管这场演出赚不赚钱,只要有收入就必须支付一定比例的版税。
绝大多数的剧组主创都有版税收入,导演是最多的,一般在2。5%左右,少的如灯光师,可能只有0。3%。
另外主创们还会分到一定的利润分成,利润分成是指在演出有盈利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的分成收益。
根据行业规则,一部舞台剧84%的利润是由制作人所带领的投资人团队获得的,人家拿出真金白银来投资,承担失败风险,拿利润大头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剩下的16%则是由剧组的主创们按照贡献进行分配。
一般百老汇比较优秀的编剧能拿到的版税收入和利润分成都在2%和1%左右。
林朝阳身为《父亲》的原著作者和中文版话剧的编剧,拿到的是5%的版税收入和3%的利润分成,比行业标准高了一倍还不止。
而他拿到的这份酬劳,除了因为他的版权费收得很低,主要还是名气够大。
事实证明,尼德兰德公司当初的选择也没有错,和林朝阳合作,为他们公司再度创造了一出经典剧目。
也许是因为第一次进军制作领域就取得了成功,乔治格外兴奋,兴致勃勃的给林朝阳算起了未来他能取得的收入。
按照百老汇的演出习惯,工作日每天一场演出,中间固定休息一天,周六日是每天下午、晚上两场演出,每周八场演出。
以《父亲》的受欢迎程度,演满整个演出季不成问题,哪怕后期上座率下降,票房突破2000万美元也不是问题。
仅此一项,林朝阳就将获得100万美元的版税收入,如果再算上3%的利润分成,这个数字可能要超过140万美元。
“听起来可真不错!”
面对乔治口中吐出的数字,林朝阳内心毫无波澜,但还是很给面子的称赞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