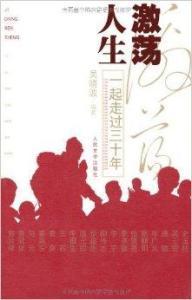紫夜小说>女眷送往军营 > 第23章 设局之人(第1页)
第23章 设局之人(第1页)
是呀,为何小姐数血点时,那功德幡幢为何又突然多出一个周字来?”怜双道,“奴婢当时瞧得仔细,小姐当时虽然触碰了幡幢,但手指上并未有任何血迹。”
宋十鸢对纤云道:“你去取一些姜黄粉过来。”
很快纤云取了姜黄粉回来,宋十鸢把姜黄粉倒在一张白色的帕子上,取出未用完的碱水,拔掉瓶塞将碱水洒了上去。
那些姜黄粉立时变了色,似血水一般浓稠黏腻地沾在手帕上。
几人看着这一幕,面露惊讶,都好奇地看着宋十鸢,等她解惑。
宋十鸢解释道:“了智所用的功德幡幢是用姜黄浸泡染过色的,这姜黄染料只要一遇到碱水就会变红,似鲜血一般。”
“原来如此,他那幡幢刚好是黄布,寻常人根本自然察觉不到。”谢嬷嬷感慨道,“真是没想到那德高望重的了智,一手批命之术令西京权贵趋之若鹜,竟是这样骗人的把戏。”
纤云了然:“难怪小姐说叫人煮了黄姜茶,那了智就被捉住了命脉一般,顺着小姐的话音告诉老爷八字是真,命卦就做得了准。”
怜双仍有疑惑:“可奴婢并未瞧见那了智用手指触碰幡幢,他是何时将碱水弄上去的?”
宋十鸢擦了擦手上沾到的姜黄粉,道:“你们可还记得他在给母亲批命之前曾净过手,那钵盂里盛的应当就是碱水,他手腕上戴了一串佛珠,我仔细看过那佛珠的取材是杉木,杉木质地较轻,本不适合做成佛珠佩戴,但杉木吸水吸湿性极强,他给母亲批命时,功德幡幢停转时曾用手腕擦碰过幡幢。”
几人恍然大悟,也有些惊叹于宋十鸢竟观察得这般仔细。
纤云道:“难怪那幡幢上只有七个点,竟是用沾了碱水的佛珠擦碰出来的。”
怜双愤然骂道:“这该死的秃驴,也不知是受了谁的指使,竟算计咱们夫人!”
“是周氏?”谢桐问出声,她原先还以为自己的命格当真克到了子女,才会使得十鸢一出生便痴傻,这会知道了智神乎其神的批命之术不过是这样简单的伎俩,自然不会再相信。
宋十鸢道,“我没有任何凭证,但只看这一桩事后的获利者,应当就是周氏母女无疑,倘若不是她们,那便只能是父亲。”
但宋怀壁的反应,明显不像是设局之人。
命卦强调谢桐克丈夫仕途,背后算计之人明显是想让宋怀壁休妻,给宋怀壁休妻送上一个极为好用的借口,谢桐被休,能得到好处的只有周氏母女,所以宋十鸢才会将祸水引到周氏的头上。
谢嬷嬷赞叹道:“好在小姐急智,一眼就看穿了那了智的把戏,才能及时化解,不然,夫人还不知要被外头那些人如何非议。”
她顿了顿,又说道,“不过那几位夫人恐怕会以为是咱们夫人故意为之,用这样的手段来针对那周氏。”
谢桐不是很在意地道:“随外面那些人怎么想,即便我什么都不做,来日任由那周氏进府,落下个大度的名声就好听了?你瞧宋怀壁方才那跳脚的样子,真是可笑。”
她这个明媒正娶的正室,却被丈夫贬得一文不值,竟是样样都不如那周氏可心。
谢桐都有些恍惚地觉得当年不是宋怀壁死乞白赖地要求娶她,而是她强迫宋怀壁娶了自己。
“小姐,你既然知道了智批命的骗术,为何不当场揭穿了他?”怜双问道。
宋十鸢喝了口茶,缓缓说道,“了智靠这一手批命之术在西京声名鹊起几十年,先时纤云也说过,就连当今皇后的凤命都是了智批出来的。倘若我揭穿了他,那些被他批了命格不好的人固然欢喜,恼恨了智行骗,可诸如皇后一般的达官显贵呢?他们只会怨我多管闲事揭穿了智。”
谢桐赞同道:“鸢儿说的在理,思虑的更为周到。”
她又问道,“鸢儿,你怎知姜黄染色后的幡幢遇见碱水会变得血红?”
宋十鸢心内一紧,但神色未变,说道:“女儿从前痴傻时不是喜欢听话本吗?我也忘记在哪个话本里听到过有道士用木剑刺符纸出血,是因那符纸先用姜黄染过色,再用沾了碱水的木剑相刺,如此便会见血。”
怜双用力回想:“奴婢给小姐念过这样的话本吗?奴婢都不记得了。”
纤云点了点她的脑门:“这些年给小姐读的话本太多,咱们过眼不过心,你自然记不得了。”
宋十鸢笑了笑,继续道:“瞧见幡幢上莫名出现血红色的斑点,女儿便想着兴许与话本里道士招摇撞骗的把戏是一样的,就让纤云准备了碱水试上一试,若是不奏效,那便直接换上周氏的生辰八字,也能解决事态。”
谢桐摸了摸她的头,心中慰贴地厉害,温声道:“幸好鸢儿记性好,脑子又聪明灵活,不然……我恐怕就要与五皇子和魏大姑娘一个下场。”
宋十鸢温柔而坚定地道:“不论发生什么事,女儿都会站在您这一边,前十五年您护着我,往后我护着您。”
这话太窝心,谢桐鼻子一酸,眼底弥漫上湿意。
宋怀壁有多令她失望,女儿就有多令她感动。
今儿碧梧院发生了这么多事,长子宋允都未曾过来看上一眼,反倒是女儿处处维护,将她护在身后,为她出头。
谢嬷嬷看了一眼外头已经昏暗下的天光,出声道:“夫人,天色已晚,老奴去叫厨房摆饭吧。”
谢桐颔首,在西厢房用过饭后,谢桐盯着宋十鸢用下汤药,才带着谢嬷嬷回了正房。
“你去一趟明心阁,看看宋允在做什么。”回到房里,谢桐朝谢嬷嬷吩咐道。
谢嬷嬷猜出她的心思,斟酌着问:“可要将大公子请过来?”
谢桐叹息一声,终是摇了摇头。
片刻后,谢嬷嬷回来了,她道:“大公子的贴身小厮进忠说大公子今儿一整日都关在书房里写文章,说是张显大儒交待大公子写五篇策论。”
见谢桐面露失望之色,谢嬷嬷宽慰他道:“大公子应是专心做文章,并不知晓碧梧院生出的是非,才没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