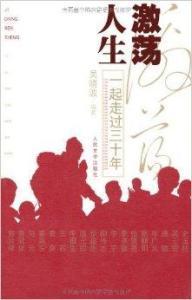紫夜小说>暴君的笨蛋男宠带球跑啦免费阅读 > 第35章 例外(第3页)
第35章 例外(第3页)
萧权川负手道:“出来吧。”
一个粗壮的男人从角落探出头来,笑得憨厚老实:“嘿嘿,陛下怎么知道我来了的?”
不就是武相任潜吗?
“昨夜元嫔一事出动了这么多兵力,你怎会不知道?按你那尿性,不进宫视察一番,改变布局加强巡防,估计今夜要睁眼到天光。”萧权川心如明镜似的。
任潜咧嘴一笑:“高页这群野狗,以前到处乱咬人,这回陛下拿元御史开刀,总算乖乖闭上嘴巴了。”
“舒坦了吗?”
“那肯定啊!爽死了!以前我刚上任的时候,别提多憋屈了!处处被这些旧皇党阻挠,嘴巴又说不过他们,每次只能干吹胡子直瞪眼。”
萧权川没功夫与他闲聊:“我让你查的事呢?”
“哦哦,”任潜从袖口掏出一沓纸,“按你说的,每一桩写得明明白白,缘由、过程、证物、证人都在这儿了。”
说起此事,任潜气不打一处来:“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那个元嫔居然还和元御史牵线搭桥,春闱舞弊中,就有人是通过元嫔认识的她爹,介绍一个收五十两,可若想拜入元家门下,就得另交四百两!”
“你是不知道,那元家有个地下室,以白银为床,以金子为墙,我的眼睛差点被闪瞎了。他娘的!我一年也就一百八十两!”
萧权川从书信里抬眸看来,拎出两个字眼:“也——就?”
任潜被盯得后背发麻,立即变脸道:“我有说吗?没有吧?我认为啊,为官者,重在廉洁亲民、民信民爱,钱这种身外之物,一点都不重要,对吧陛下?”
萧权川懒得理他。
“不过陛下,元御史这般罪孽深重,你真打算就这么放他平安无事地告老还乡啊?”任潜不服道。
萧权川摇摇头,不知一语,执笔点墨,姿态端正,行云流水在空白信纸上写了一行字。
随后迭起来,行至一扇墙前,撩开一幅山河挂画,将信纸塞进上边砖缝隙里。
咔嚓一声,好似有什么机关吞掉了那封信。
又是咔嚓一声,那块砖的下缝隙吐出一张迭好的纸条,萧权川自然而然拿走,放下挂画。
任潜知晓,那是皇帝与天密阁通信的渠道。
后知后觉,他微微睁大眼睛:“难道是……截杀令?”
萧权川眯起墨绿色的眼眸:“你猜?”
起风了,元家……要没了。
须臾,他听见萧权川忽然骂道:“混账!”
“骂我干啥???”
话音未落,萧权川一举捏皱纸条,狠狠扔掉,板着一张脸,大步流星离开南书房,浑身戾气,倘若塞给他一把利刃,照这般杀气,上阵以一敌千绝不为过。
任潜一脸懵然,嘀咕道:“发什么疯?”
他好奇极了,拾起那张皱巴巴的纸团,展开一看,眼珠子险些双双掉下来。
他刺溜一下追了出去:“陛下!陛下!冷静点!”
不知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睡了多久,姜妄南睁眼醒来时,窗户上遮光的布帘已经撤走了。
这一觉,睡得格外安稳。
香炉袅袅生烟,整个宫殿流动着淡淡的木质龙涎香,闻起来身心舒适,似有安神之效。
“秋若?秋若?”
秋若从外疾步走来:“娘娘醒了?”
他舔舔干燥的唇:“嗯,我好像有些饿了,有吃的吗?”
“有,不过,太医说了,娘娘醒来后,还要再把把脉。”
“好,帮我倒杯水吧。”他不以为意道。
不多久,秋若神情不安地引着太医进来。
“有劳太医了……咳咳咳。”姜妄南堪堪抬眼,猛然被嘴里的一口水呛到。
“刘……”
“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