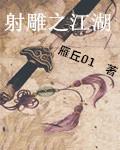紫夜小说>回到六零开网店格格党 > 第55章 陈家村被点名表扬(第2页)
第55章 陈家村被点名表扬(第2页)
“是不是电视台也来?我得找干净衣裳穿!”
“我家门口的柴火堆得赶紧拾拾,别丢人现眼。”
而此时的陈鹏飞,正在镇供销社对接下一批包装物料的事。接到陈支书的电话后,他连忙带着文件回村,半路上就被村民们围住。
“鹏飞,这事真的假的?”
“省里点名,咱真成了模范?”
“你可不能跑啊,电视来了得你出镜!”
陈鹏飞一路笑着应付,回到大队部,会议已经开始。芳兰坐在旁边记录,陈支书拍着桌子道:“这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大是我们机会来了,小是我们可不能飘。接下来三件事:一是村貌整治,二是企业展示,三是村民访谈,谁都可能上电视,都别出岔子。”
陈鹏飞补充:“样板村,不是样子货。咱的蜂蜜罐头,质量、流程、品牌,样样得硬。尤其是产品展示区,必须一天打扫两次,瓶盖朝向都要统一,不能让人挑出茬来。”
“同意!”芳兰在笔记上重重画了圈。
……
三天后,省农业厅考察组、电视台、报社记者,以及省供销社、农技总站共计十余人,浩浩荡荡进村。
陈家村的大路旁挂起了欢迎横幅,罐头厂和蜂场门口都立起了展板,女工们统一着装,蜂箱排布整齐,祠堂门前还用老苹果树枝编了花架子,陈鹏飞亲自站在门口接待。
“欢迎各位领导、专家、媒体朋友莅临陈家村!”
考察组成员下车后,先到罐头厂车间,芳兰亲自讲解生产流程。她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了罐头制作从选果、杀菌、封装、贴标到入库的每个步骤,不卑不亢、不急不躁,赢得考察组连连点头。
“你们这个包装是自主设计?”
“是,结合陈家村自然形象与产品属性定制的。”芳兰答。
“瓶盖标签怎么做到误差不超过1度?”
“全村统一流程,贴标前泡水一晚,晾到七成干,模具压标,全手工对齐,每十瓶抽检一瓶。”
“厉害。”摄影记者连连按快门。
随后考察组前往蜂场。老蜂箱一字排开,操作间内整洁干净,村民们正在进行筛蜜与装瓶作业。
“这一排是高产箱,编号001至020;那一排是新蜂试养区。”陈鹏飞带头介绍,语气平稳,神态自如,“我们今年夏季产蜜七百斤,其中一级蜜占七成,已全部入市销售。”
考察组成员蹲下看了一眼蜜箱里的蜂群,点头称赞:“你们这不是农户养殖,是标准化生产了。”
最后一站是祠堂展区,陈家村的“振兴之路”被制作成展板:从第一瓶罐头试制,到第一单订单、第一份品牌认证、第一封省级电报,一步步记录清楚,照片、实物、数据一应俱全。
电视台女记者看得入神,忍不住问:“这真是一个贫困村干出来的?”
陈支书咧嘴一笑:“不是干出来的,是逼出来的——山太高,路太远,年轻人都跑了,咱要是不想个法子,就得穷到老。”
镜头一转,芳兰正在为村民讲贴标技术,孩子们蹲在门口听得出神,镜头中,她一身素衣,神态坚定,背后是罐头成品堆成的小山。
采访结束,记者拉住陈鹏飞:“你们两个怎么想到带动全村人一起干?”
“因为我们俩一个人干不了。”陈鹏飞说,“也因为我们想让村里人都能留下来,不用外出打工,不用抛家舍业,孩子在村里能上学,老人能吃上自家做的果子罐头。”
当天晚上,《省农经报》发布专题报道:《蜜果香·陈家村崛起记》,其中一段写道:
“在秦岭深处,一个曾经籍籍无名的小村庄,正以蜂蜜与罐头为起点,跑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产业振兴之路。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奇迹,而是一场脚踏实地的探索——他们没有资本,没有技术背景,有的只是一群肯干的人,一点一滴拼出来的信任与制度。这,就是陈家村。”
电视台报道播出那晚,整个村都聚在大队部看电视。
屏幕里出现陈鹏飞讲解蜂箱,芳兰操作封罐机,陈奶奶削果皮,孩子围着蜂箱转圈,甚至还有陈支书背着手走在晒场上。
那一刻,村里安静得出奇,谁都不说话,眼睛一眨不眨。
直到片尾出现“省级重点支持单位——陈家村”,全村掌声雷动。
陈鹏飞坐在人群中,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翻江倒海。他知道,这是起点,是肯定,也是新阶段的开始。
芳兰轻轻拽了拽他的衣角:“回家吧,厂子明天还得开工。”
他点点头,站起来,又回头看了一眼还在播新闻重播的屏幕。
“兰子,你说——咱要是再干几年,是不是能真的留住人?”
芳兰一愣,继而认真回答:“能。”
陈鹏飞没再说话,只是望着那台泛光的电视,像是望着一个沉甸甸的未来——那不是一瓶蜜、一罐果那么简单,是一条通往尊严的路,是陈家村,真正属于自己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