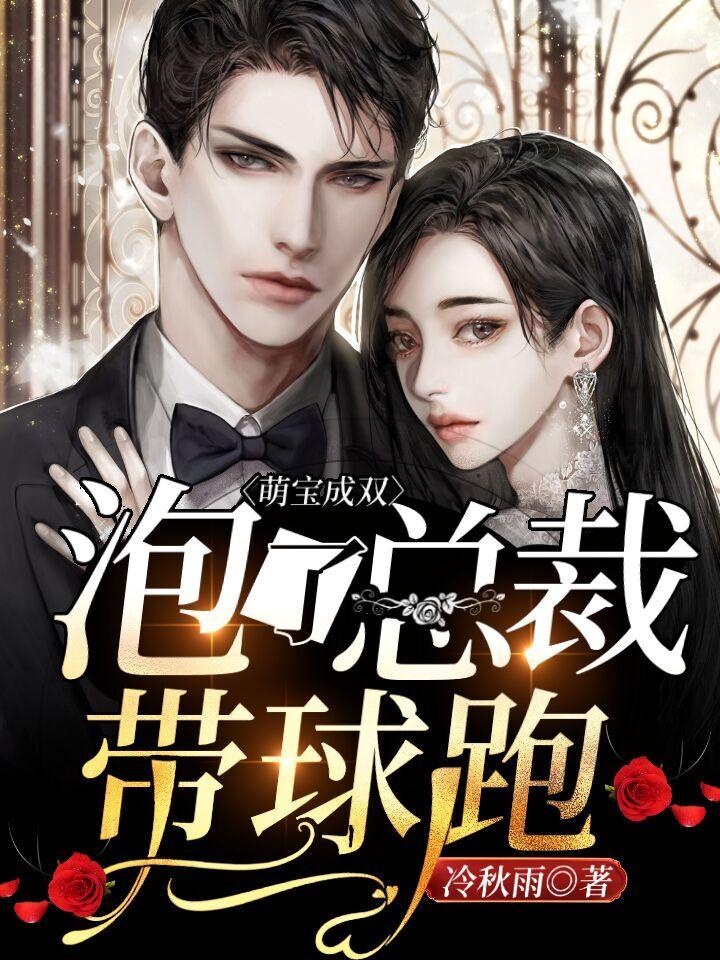紫夜小说>重回六零我带着淘宝无敌了 > 第58章 村庄的誓言(第2页)
第58章 村庄的誓言(第2页)
那天下午,镇领导带着几位建设办干部上门实地查看。
“陈家村动作真快,这批开工点是全镇第一个开建的。”
“你们这个合作社升级方向很好,建完了之后,可以申请镇‘农村社区产业试点项目’,我们那边资金上再往上推一推。”
“设备预算报上来,我们找对口单位扶一扶。”
陈鹏飞把这些话一一记在小本上,回头就安排魏局对接,白主任帮审设计方案。
这年初一过,陈家村节奏明显变了。
老百姓不再只关心哪家猪杀得肥,而是关心新厂房啥时候封顶、自己家那小子能不能进技术班、今年分账能不能再多一点。
而陈鹏飞、芳兰这一对“厂长搭档”,也从一个合作社的代言人,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带头人。
他们不再只是管罐头瓶贴没贴正,而是要考虑——下一季订单怎么接?厂区食堂怎么扩?技能工人如何培养?外地市场怎么开?
他们不再是被政策推动的一环,而是要主动推动村政策、调人心、拉资源的轴心。
陈鹏飞也终于有了他的第一张“企业名片”——
陈家村蜜果合作社·运营负责人:陈鹏飞
这一张卡片,凝聚的是过去一年所有人的信任。
是那一罐罐在寒风中手工封装的山楂,是那一滴滴在秋天晾晒后飘着桂花香的蜜。
更是无数个陈家村人,在黑灯黄昏中,点起灯、挑起担、咬紧牙关向前走的决心。
……
雪还没融尽,新厂房已立起半边框架。
站在架子前,陈鹏飞抬头望着天空,手里攥着图纸,心里只剩一句话:
“这,就是我要的——不靠谁,不等谁,靠咱自己,建出来的命。”
当天傍晚,工地收工时,夕阳刚好落在新厂房半截钢架上,泛着微微的金光。陈鹏飞坐在一边的砖垛上,手上还沾着灰,工装裤膝盖处全是尘土。
芳兰端着一壶姜汤走过来,递给他:“喝点,暖暖。”
陈鹏飞接过,低头喝了一口,眼睛却没离开那座正在拔地而起的厂房。他缓缓道:“这架子一立起来,我总觉得,咱村的骨头也硬了。”
“不是硬了。”芳兰轻轻笑着说,“是撑起来了。”
“你知道吗?”他忽然侧过头,“我小时候最怕过年,因为别人家能吃肉、能放炮,咱家总是省着过。那时候我就想,哪年我要是能给咱家、给咱村带个不一样的年……”
“你做到了。”芳兰看着他,语气柔和而坚定。
他没再说话,只是把手里那杯姜汤喝完,深吸了一口气。
远处工人们陆续散去,雪地上踩出一串串脚印,厂房的轮廓在暮色中愈发清晰。
陈鹏飞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明儿继续开干,咱这个年还没过完,新账、旧账,来年都得给我一笔笔干出明白来。”
芳兰点点头:“走吧,回家。奶等着你吃饭呢。”
两人并肩踏雪而归,背影渐远,却在落日余晖下,显得格外踏实而清晰。陈家村的新年,从这片热土和脚印里,开始书写真正属于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