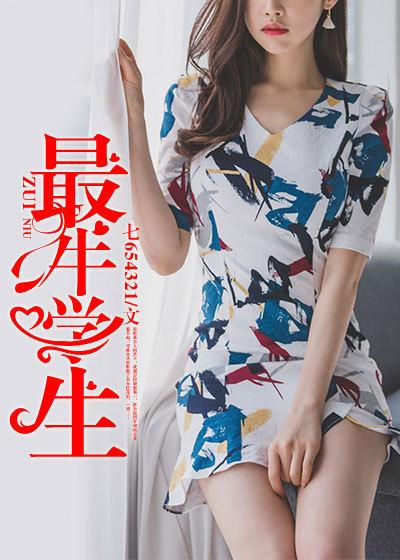紫夜小说>回到六零开网店完结 > 第56章 合作社第一次分账会(第2页)
第56章 合作社第一次分账会(第2页)
“我这辈子第一次,靠削果子赚了几十大元。”
“我家那闺女原先嫌回村没出息,现在天天在罐头组,前几天还领工资请我吃了顿饭。”
会议室一片静谧又温暖的气氛。
随后陈东站出来,代表蜂场青年组宣读收购统计:
“本年度,共收购村内蜂蜜19户,其中李家、周家、杨家产量最高,全部收购价统一为每斤6元,一级蜜加价至7。5元。加权之后,每户平均收入在三百至六百元之间。”
接着,村支书站出来压轴总结:“这第一年,能把账说清楚,大家就踏实。明年,我们将尝试把罐头厂注册成‘乡村小企业’,争取带薪工人指标,进一步扩产。只要大家愿意干,这条路,就能走远。”
……
散会后,村里人簇拥着走出大队部。人人手里或多或少拿着一张红纸信封,脸上都带着一种久违的光。
“俺家老三说回来打工,我现在看,回来是对的。”
“你看我家大妞这回多争气,年初啥也不会,现在光靠贴标签就挣了两百多。”
陈奶奶被陈鹏飞搀着回家,手里还攥着那张分红单据,嘴里一直念叨:“好,好,真好。”
走在回家路上,陈鹏飞忽然停下脚步,看着天边飘落的第一场雪。
“兰子,这账,咱们总算开了头。”
芳兰背着个布袋,笑着说:“第一年能不赔就是好兆头,能分账,就是稳了。”
“可惜的是……”陈鹏飞叹口气,“我妈还没亲眼看到。”
芳兰轻轻挽住他的胳膊,低声说:“她肯定在天上看着你笑呢。你带着全村人,把家给扛起来了。”
风吹起树梢的雪屑,落在他们头顶,白茫茫一片。
那是一个村庄冬日最静谧的时刻,也是这段长路,终于站稳的起点。
陈鹏飞沉默地站了一会儿,望着远处村头祠堂屋檐上挂着的红灯笼被风轻轻晃动,像极了母亲生前在年前忙碌张罗年货的模样。那时他总嫌母亲唠叨,嫌她做的罐头太甜、蜂蜜太稠,如今才发现,那些柴米油盐的手艺和细节,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他如今最倚重的基础。
“兰子。”他忽然低声道,“咱明年过年,就不出去买年货了。蜜、罐头、腊味,咱都自己做,自己村产的。”
芳兰“嗯”了一声,声音轻得像雪落肩头。
“还要给厂里每位工人发一盒带包装的年货盒子。”他又补了一句,“贴着‘陈家村·蜜果牌’的商标,让大家知道,咱干的,不只是工分,是咱自己的牌子。”
“行。”芳兰点点头,“你说咋办就咋办,我来安排。”
雪越下越密,村里屋檐下开始燃起炊烟,一户户人家开始为冬日里第一场雪忙碌起来。
陈鹏飞转过身,看着这一切,心里忽然很平静。
这一年,他们走得并不容易,但终究,他们撑过来了。
他们把一个落后的村庄,变成了一个能分账、有产业、有尊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