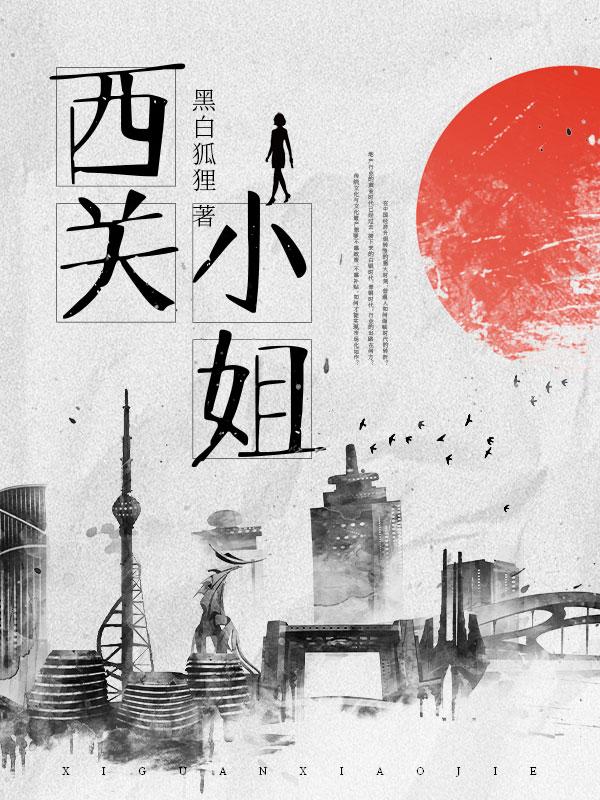紫夜小说>风波庄武侠主题餐厅 > 问天(第2页)
问天(第2页)
越东风看着他,“刚刚我跟你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我们说了这麽多话,怎知……”季千里看着他眼睛,却霎时心意相通,“……你是说那个人叫越昙?”
越东风点头。
“就是那书苑主人?”他看他神色,笑道,“我只惊讶他与你同姓。”思忖後道,“……难道是你的祖上?”
越东风点头动作稍轻。
他这人百无禁忌,当日在醉仙居放他走已是少有犹豫,季千里也未看见,此时心道,他先在外面说起还那般自如,这会儿多半是回到这里,多少有几分情怯。他爱这人风仪洒脱,然见他这般神态,心头更倍感爱怜,轻声道,“那有什麽关系,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又跟我们有什麽相干?”
“是不相干,不过越青天这个人最擅胡说八道,你别被他骗了才好。”
季千里郑重点头:“他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信。”
越东风被他逗笑,“嗯,你想知道什麽,等空了我再说给你听。”
季千里从不嫌他话多,哪时都愿听,又想当日郑家那二人甚会算计人心魔,方才那坟堆也是一般,立刻道:“那你这会儿便说给我。”
“嗯,那是……”
言语之间,二人临近一道院门,季千里咦了一声。
见那门前新栽了两排树,一是梧桐,一是垂柳。二人还离几丈,院中脚步声起,六人鱼贯走出,分列两边,盈盈一福身,柔声道,“公子来了。”
“婢子紫云。”
“婢子青女。”
那打头的一紫一青两个少女,一个姿态端方,一个仪容娇美,各都笑盈盈的。
季千里犹在方才听故事的惊讶中,方才已见过活人,这时也不那般意外了;越东风淡笑道,“姑娘这是拦路呢,还是待客?”
衆女依旧一福,紫云微微笑道,“这是公子的家,婢子只来服侍,不敢喧宾夺主。屋里备了热茶酒,公子请。”
二人对视一眼,跟在身後。
季千里又凑他耳边,“记住啦,不喝人家的东西。”
越东风莞尔,“别人给的东西,你从来没给过我,是不是?”
季千里望着他点头,“苏大夫说得对,小心驶得万年船……”
他嗯一声,“小师父说得也对,我们不贪人家的东西。”
季千里听说这是他从前居所,一路便忍不住东张西望。那院儿比一路所见都更为完整,想是最先修来,随地势曲折错落,有亭有阁,有池有鱼,藻荇交错,树影扶疏,彼此相映成彰,若不细看,便如未经火烧。里头却还有十多侍女,各都娇美非凡,有的拭笛吹箫,有的摆棋弄书,有的研墨洗笔,似只待人来用。
一见他们,都停下道,“公子。”
季千里见那梧桐垂柳时已然多看了,又见此琴书婢女,脸莫名一烫,看越东风,他正促狭看他,耳朵更红通通的。
“我们不要这许多人。”
季千里听他心情不错,也笑了笑。
然毕竟要去见那两人了,一颗心不敢再胡乱思想,随之转过十来级台阶,陡然小瀑飞流,红梅朵朵,隔着七八丈远,青山中高悬一间白石屋,想是被树瀑包围,屋架毫无损伤,其上郝然刻着“洞中客”三字。心道,难道里面是个洞。
念刚一动,二女微张玉臂,先後朝彼间去,如游蛇凌空滑移,他惊异非常,随後身子也一轻,被越东风带到彼岸。
回头一看,身後二女也都似先一般跟来。
原来此彼当中横了条白玉栏,因细如儿臂,隐在雾中,还道悬空。他转念道,不过即便有此物,要他从此细栏走过也是绝无可能,想来这些少女个个身怀武艺。
心中又是佩服,又愈警惕。
一进屋香烟氤氲,暖意融融,有榻有椅,有书有画,满目古香。小窗临翠,玉屏掩琴,一张桌上留有笔墨,右悬一幅未写完的字: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虽力微弱,其字其文却奇气纵横,放言无惮,全不露雕琢痕迹,谁人也不能把它忽略。
那左悬三轴绢画,也是同样力弱,亦着笔老道,左鹤行鸣竹林,右猿抱子栖于高松,当中白衣观音趺坐,丰腴面相,静穆神态,如梦幻显身,空明之至。
季千里见过越东风字画,仍暗赞此人笔法,又道字画似有矛盾。因那观音像着实美妙,又一望便未转睛,越东风也多看一眼,似一笑,“越青天快死了?”
紫云听他不敬,脸色微一变,“老先生自从郑家公子那里回来,是落了病根,不过先生找了药,想来没有大碍。”
他也不知是不是可惜,“从前挂的‘梅花屋主’的墨梅,忽然又问天,又参禅,我还道他终于是要死了。”
紫云装未听见後半句,温顺道:“老先生也说起,公子所作墨梅花繁不乱,风神峭拔,比梅花屋主更青出于蓝,可惜已被烧毁。他老人家念叨少了什麽,又见了公子作的‘财色名利欲’,手痒临夜摹出这三轴法常僧人的观音猿鹤图,特地让人送来。”
青女亦道:“这幅屈灵均的《天问》,因他老人家体力不支未写完,他交代公子喜欢,刚好帮他填一填。”
那边上果真还馀半白。
越东风淡哼一声。
![(历史同人)[汉]穿成武帝家的崽+番外](/img/23399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