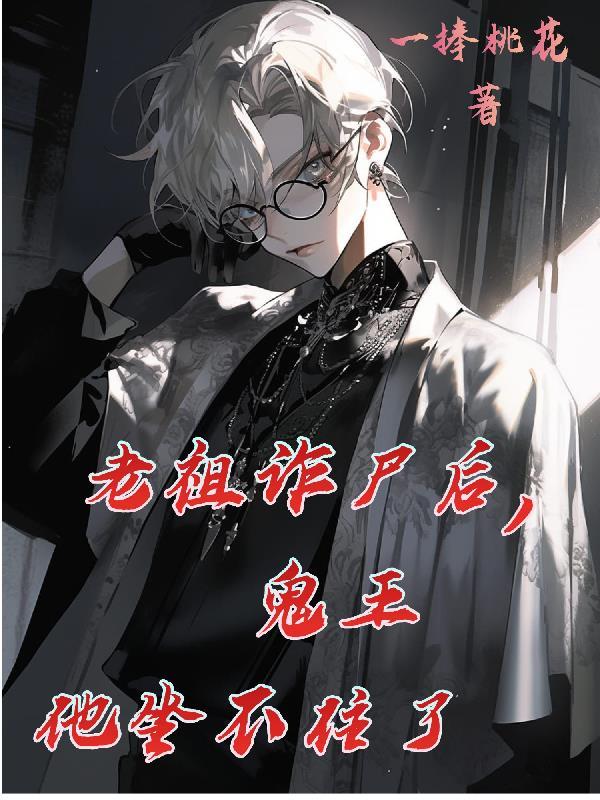紫夜小说>学生闹翻天完整版 > 阴谋阳谋10(第2页)
阴谋阳谋10(第2页)
话音落下,资料室里的气氛瞬间严肃了不少。尹柏萧皱起眉,手指无意识地敲了敲桌面,桑矾逸也收起了轻松的神色,显然都明白苏邴哲那股子执拗劲儿——一旦盯上什麽事不查个水落石出是绝不会松手的。
叶馨蒙恰好路过资料室门口,里面传来的对话一字不落地钻进了她的耳朵。她脚步一顿悄悄停下,侧耳听了片刻,随即转过身,双手环抱在胸前,眼神里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嘴角勾起一抹若有所思的弧度。
“看来他们的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外面的风波上了。”她在心里默默盘算着,指尖轻轻敲击着自己的胳膊,“这样正好……我可以继续在内部安心‘搞事’,没人会轻易察觉到这边的动静。”
正所谓外部风雨如晦,仿佛有无数看不见的浪潮在暗处汹涌翻滚,每一次波动都可能掀起惊涛骇浪;而内部却看似如一潭止水,表面平静得像面光滑的镜子,没有丝毫波澜。然而这层平静之下,暗流从未真正停歇过,它们在无人察觉的角落悄然涌动,裹挟着各种隐秘的心思与未说出口的盘算。表里之间的巨大张力在沉默中不断积蓄丶膨胀,就像拉满了的弓弦,只需要一个微小的裂隙,哪怕只是一道细微的划痕,便能瞬间冲破所有刻意维持的假象,将那层脆弱的安宁彻底颠覆。
叶馨蒙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底的波澜,不动声色地转身离开,脚步轻得像一片羽毛,仿佛刚才那个驻足倾听的身影从未出现过。
当夜。女护工又俯身用抹布仔细擦拭着走廊两侧的候诊长椅。她的动作轻柔而专注,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光滑的脸颊在微弱光线下仿佛自带柔光。四周静得能听到抹布纤维与塑料椅面摩擦的细微声响。
“叮——”
电梯门滑开。外科医生秦俊珩迈着略显疲惫却依旧稳健的步伐走了出来。他刚结束一台紧急阑尾手术,手术服外套着白大褂,脸上带着一丝手术成功後的松弛感。看到正在忙碌的女护工,他停下脚步,脸上露出一个爽朗而友善的笑容。
“辛苦了。”他的声音在寂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洪亮,带着外科医生特有的那种直接和大气。
她闻声直起身转过头。看到是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医生,脸上立刻浮现出那个惯有的丶温和而略带距离感的微笑。
“工作职责所在。”她轻声回答,语气平和,既不显得过分热络,也没有失礼。
秦俊珩点了点头,目光很自然地在她脸上多停留了几秒。或许是刚结束高度紧张的手术,视觉记忆还处于活跃状态;或许仅仅是眼前这张脸确实过于出衆。一种模糊的熟悉感像水底的气泡,悄无声息地浮上他的心头。
他微微歪头,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带着几分外科医生的探究神色坦诚地说道:“看着有点面熟……我们好像哪里见过?”
女护工脸上的笑容没有丝毫变化甚至连嘴角的弧度都未曾改变。她迎着他的目光,那双深黑色的眼睛平静无波,回答得流畅而自然带着恰到好处的一点茫然:
“是吗?我看是第一次见吧,医生。”
她的反应无懈可击。一个刚来不久的新护工,被一位资深医生认错或觉得眼熟,用这种略带不确定的否认来回应,再正常不过。
果然秦俊珩被她这麽一说,反而有些不确定了。他擡手揉了揉後颈,努力在记忆库里搜索了一番,但那点模糊的印象就像抓不住的烟雾,稍纵即逝。他确实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这张脸。
“噢……”他笑了笑,带着点自嘲,“可能是我记错了,或者你长得比较大衆脸?”话一出口他就觉得不对,这张漂亮的脸,怎麽看都和“大衆”二字不沾边。“哈哈,开个玩笑,别介意。忙你的吧,早点休息。”
他朝她摆了摆手,不再纠结这个小插曲,转身朝着医院大门走去。
“医生慢走。”她在他身後轻声说道,脸上的笑容在他转身的瞬间便悄然隐去,恢复成一片深沉的平静。她重新弯下腰,继续擦拭着下一张长椅,动作没有一丝停顿或紊乱。
秦俊珩走出医院,深夜的凉风让他精神一振。他大步走向停车场,找到自己的车,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车内很安静。他插入钥匙,却没有立刻发动引擎,而是靠在驾驶座上,眼前又浮现出刚才那个漂亮女护工的脸。
光滑的额头,挺翘的鼻梁,那双格外漆黑沉静的眼睛……尤其是那种混合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疏离感和熟悉感的气质……
“确实面熟啊……”他低声自语,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方向盘,“但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在哪儿呢?”
是某个病人的家属?以前在其他医院实习时见过的护士?或者是某次医学会议上有过一面之缘的同行?
他努力回忆,但记忆就像蒙上了一层磨砂玻璃,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细节全然不清。那种感觉令人有些烦躁,就像是一个呼之欲出的名字卡在喉咙里,偏偏就是说不出来。
最终,他摇了摇头,放弃了。也许只是错觉,也许是疲劳导致的记忆错乱。医院里人来人往,看到长相相似或者有既视感的人,并不算什麽稀奇事。
他发动汽车,引擎的轰鸣声打破了停车场的寂静。车灯亮起,划破黑暗,载着他驶离了医院。
只是,那张在昏黄灯光下平静微笑丶却又带着某种深不可测气息的脸,像一个未解的谜题,短暂地停留在了外科医生秦俊珩的脑海深处,随着车轮的滚动,渐渐沉入记忆的底层等待着以後到来丶被唤醒的时刻。
阴暗的密室仿佛被这突如其来的怒吼震得簌簌发抖。托尼亚猛地一掌狠狠擂在厚重的实木桌面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震得桌上的台灯丶文件乃至空气都似乎跳了一下。
“废物!一群废物!”他额角青筋暴起,因极度愤怒而扭曲的脸在昏黄灯光下显得格外狰狞,“孤狼那个蠢货落在他们手里!我们的计划……全暴露了!你看你选的什麽人,丢人现眼就是一个蠢货!”
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些话,每一个字都裹挟着炽烈的怒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丶计划脱离掌控後的惊惧。失败的耻辱和对後果的恐慌交织成一条毒鞭,狠狠抽打着他的神经。
站在阴影里的杰卡身形绷紧,大气不敢出直到托尼亚的咆哮暂歇,才小心翼翼地开口,声音干涩:“接下来……我们该怎麽办?”
托尼亚猛地转过身,胸膛剧烈起伏,眼中闪烁着毒蛇般的冷光,所有的暴怒在瞬间被强行压抑丶淬炼成更危险的狠戾。他几乎没有丝毫犹豫,从齿缝间迸出冰冷的指令,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啓动二号线!”
托尼亚的怒吼在逼仄的密室里回荡,震得空气嗡嗡作响。他眼中布满血丝,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困兽,计划暴露的耻辱和失败带来的连锁反应几乎要将他吞噬。
面对上司的震怒,杰卡却像一块浸在冰水里的岩石,纹丝不动。他沉默地等托尼亚的喘息稍平,才用那种特有的丶毫无波澜的声线开口,每一个字都冷静得近乎残酷:“不能啓动二号线。绝不能,”
托尼亚猛地擡头,凶狠地瞪视着他。“你说什麽!”
杰卡无视那几乎要杀人的目光,继续有条不紊地分析,像是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孤狼被捕,意味着瑆洲的情报系统已经被彻底惊动。他们现在不单是警觉,还已经炸开了锅,接下来必定会进入最高等级的战时戒备状态。所有通道都会被严密封锁,所有可疑人员和行动都会受到最严格的审查。”
他微微前倾,昏黄的灯光照亮他半张毫无表情的脸:“在这种时候强行啓动二号线,风险远超收益。我们的人极可能在行动前就被锁定,甚至可能落入对方设好的陷阱。届时即便我们侥幸得手……”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也绝对无法脱身了这等于把我们最精锐的力量送去给对方围歼。结果占不到任何好处,反而是彻底的赔本买卖。”
托尼亚听着他冰冷的话语,胸中的怒火被更深的无力感取代,他颓然一拳砸在桌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咬着牙低吼:“那怎麽办?!难道就这麽算了?上面的怒火,谁来承担?!”
杰卡的嘴角似乎极其细微地向上扯动了一下,但那绝非笑容,而是一种冰冷的算计。
“当然不能算了。”他的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种毒蛇吐信般的嘶嘶声,“我们需要一个折中的法子。”
“一个……无论成败,我们都能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子。”他眼中闪过幽光,“赢了,我们自然获利,达成部分目标,足以向上面交代。即使输了……”
他刻意停顿,让那意味深长的沉默在空气中弥漫,然後才缓缓道:“……也必须确保我们能及时丶干净地脱身。甚至,可以把失败的原因,‘合理’地引向别处。最重要的,是保住我们的根本,避免更大的损失。”
“我们要做的,是下一盘看似冒险,实则无论棋局如何,我们都能抽身而退的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