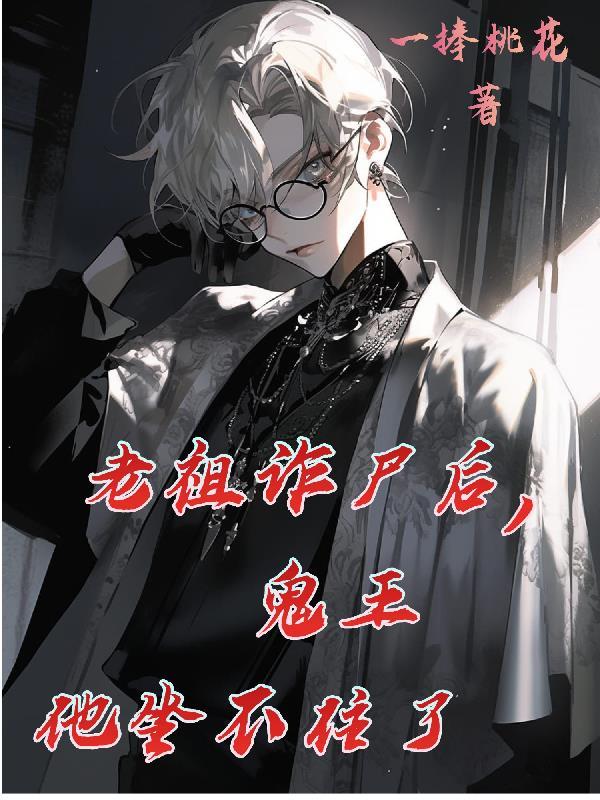紫夜小说>网络用语白月光 > 第235章(第1页)
第235章(第1页)
光是想到谢景骁的脸和会说出这样的话的语气,李灼就觉得自己的心已经生气得快要爆炸了。如果真让他在家发现谢景骁,他一定会结结实实把他揍一顿。可惜找遍了所有房间,连平时没怎么去过的二楼,三楼都找了一遍,也没有找到混蛋谢景骁的影子。他从楼上下来的时候,看到小梅和物业保安站在客厅。“李先生,是你回来了啊。”小梅看到是他,连忙和保安道歉,说这个人是业主。小梅煮了茶水招待他,“我刚才听到家里有脚步声,以为是有人从露台进来了,我有点害怕李先生今晚睡这边吗?我去铺床。”李灼说不睡:“谢总去哪里了?”小梅摇头:“我也不知道,张管家就给我打了电话,让我过来照顾小鹦鹉。”“张管家什么时候给你打的电话?”“八月底的时候,我记录过是8月27号”小梅拿出手机看了看日历:“因为来这边的工资会比在庭院高几百块,我都有记录。”8月27号,也就是温欣举办画展的第二天。李灼找小梅要了张清秘书的联系方式,又问她豆苗和芸豆还好吧?“它们两个叫这个名字啊。”小梅惊讶的说:“我叫它们啾啾不过只剩下一只青色的啾啾了。”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去吧去吧,到觉悟的地方去,走过所有的道路到彼岸去,最终到达彼岸)在诵经的时间,谢景骁会跟着师傅与信众们一起练习,明明听到了,嘴唇也能够蠕动,喉咙里的声音却无法发出来。有时候谢安儿不用上学,会一个人到他的禅房看漫画书,他说哥哥你一个人太无聊了,我过来陪陪你吧。他有时候也会看谢安儿带来的漫画书,他看不懂对话框里的字,只好专注的看图片,他发现只靠自己猜测也无法明白故事究竟在讲些什么,他就放下漫画书,凝望窗户外面,对着庭院里的菩提树发呆。一个人的时候他总会回忆失语发生的开端。如果用语言表达,一定不会有人相信,他是依靠一种准确的直觉观察到,“它”又来了。他看着李灼气呼呼的转身就走,他甚至连上去阻拦的机会都没有。如果这件事暴露出去,只会更糟糕。他记得他在准备离开会场前,有一个志愿者很关心的问他,是不是感觉不舒服,感觉晕眩,茶水间有饼干和蛋糕,可以随便取用。他做了一个拒绝的手势,冷静的从会场离开,中途有零星的客人和他打招呼,他冷着脸没有回应,他想大概给人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他在车库找到坐在车内休息的司机,他用手势让司机从车上下来,自己坐上驾驶位。这是他的私人司机,有着极高的职业素养,没有露出任何不理解的表情,只是完美的执行。抓稳方向盘已经用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他在主干道以最低速行驶,公路上没有人知道这辆劳斯莱斯的司机在想什么,全都避让着它行驶。他回到家,用手机拨出刻在记忆深处的号码,声音沉着的男人在电话那头问他发什么了什么事,他尝试着想要说出哪怕一个单词,这样的努力都让他觉得如窒息一般的痛苦。在自己没有任何响应的电话挂断后,张清秘书搭乘了最末班的航班赶到了海城。芸豆被小梅送到了宠物医院,她说怎么喂它都不肯吃东西,好像下定决心要绝食一样,小梅没有办法,只好把它送到收治异宠的医院,让医生用很细小的注射器每天打营养液维持生命。小小的芸豆站在异宠医院的笼子隔间里,它的病友有兔子,荷兰猪,蜥蜴,医生告诉李灼从检查的结果来看身上没有任何病变的现象,根据现在已知的情况看,大概是高敏类动物群体常见的分离焦虑。它们离开熟悉的主人后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狂躁,抑郁,绝食,自毁倾向。很遗憾,在野生种群里动物不会出现这样的表现。这是人类社会强行改造物种生活习惯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恶果。从医院出来后,他请小梅再照顾豆苗几天,不过不会太久。寺庙里的生活很有规律。十一月,气温越来越低,走在户外已经要穿很厚的大衣。附近市场的摊主谢景骁很多都和他们混了个脸熟,早上市场门口会有一些卖蔬菜水果的散摊,谢景骁总会去光顾,不是一定要买点什么,只是他觉得自己不能总是囿于小小一间禅房里。每周他会去医生那里两次,车从城市的这一头开到那一头,医生给他做了卡片,帮助他恢复语言的能力,但是进度很慢,医生鼓励他不用担心,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事其实是在看不见边界的沙子地里寻找你丢掉的贝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