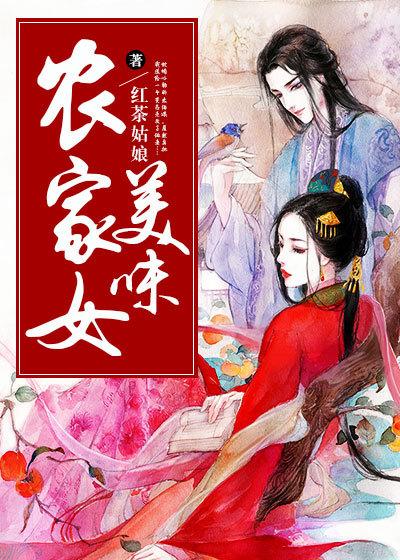紫夜小说>千秋宴上我将不爱吃的菜扔到一旁摄政王 > 第七十二章 少年意气(第3页)
第七十二章 少年意气(第3页)
次日,舟歧巡营放回,忽听兵卒大喊‘仪军来了!’‘仪军来了!’,他不由得一惊,急忙拔刀前去会战。
来到岸边,一衆兵卒拨开芦苇丛,才发觉黑乎乎的水面上只有一叶小舟,小舟上插着一根木杆,木杆上缠着一段缣帛。
舟歧将缣帛取下,仔细探看帛上言语。
他瞧了许久,发觉帛上只有八个字,不由得大怒,立马扯碎了缣帛,狠狠的扔进了河水之中。
“将军,何故如此恼怒?”部下不明,便关切似的问了一句。
“………………”
舟歧未答,愤愤的转过身子。
方才瞧到一眼的兵卒拦下那人,低声在他耳边说了几个字,那人听後,眉头皱了皱,接着叹了口气。
“诶!百主,百主!”
那人听後,转身回望。
“那帛上究竟说了些什麽?”
“夜入三更,何不安卧?”
“嗯?”
兵卒擡头看了看明月,而後轻笑一声,问道:“明月高悬,百主如何不卧?”
“…………”
百主叹了口气,接着压下声音说道:“是‘夜入三更,何不安卧?’”
“承蒙百主关怀,既如此,那末将便去安卧了,百主也得早些歇息才是,勿要损伤己身。”
说罢,兵卒匆匆而去。
百主叹了口气,略显无奈的扯了一下嘴角。
本以为此次送书只是偶然,却不想第二日,刚入了夜,便有兵卒之声传入帐中,忙喊着与昨日相同的话。
舟歧听了,为怕是计,便像昨日一般驻守在河边。
此次仪军并未送书,只将几叶扁舟送来,每叶扁舟上都站着一个草人,草人头顶上顶着‘南’字,身上的麻布也与南军盔甲颜色相近。
“此乃何意?”部下并不十分明白,反倒摩挲着下巴细看起来。
舟歧冷笑一声,指着草人说道:“还能有何意?草人不过六个,意在指出我等兵力悬殊,寡不敌衆,用稻草扎成我军的样子,是在明说我军皆是残兵败将,酒囊饭袋,不需仪军费力,便如草一般不堪一击。”
“云犁与玉子骁二人如此挑衅,当真不把本都尉放在眼里吗?”
衆将左右瞧了一眼,急忙劝道:“都尉,说到底也不过是区区挑衅罢了,都尉不必挂怀,一切还是当以战事为重,切勿因小失大啊。”
“因小失大?”舟歧回身,缓缓走向营地。
“他二人的计谋,本都尉一眼便可识破。”
“计谋?”
舟歧回头,望向江水上的扁舟,说道:“此计意在麻痹我等,只叫我等以为仪军不会贸然从水路进攻,而後趁此间隙,打我军一个措手不及,真乃可笑!速速传令,连夜加紧巡视,派出重兵把守。”
“是!”
兵卒刚走出几步,舟歧又急忙将他唤住。
“等等……无需去传令。”
“将军这是?”部下眉间似有几分不解。
“一如往常便是,只待兵卒来报,衆将再随我杀出营寨,免得打草惊蛇。”
晚风吹过舟歧的发尾,他大笑几声,接着便转身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