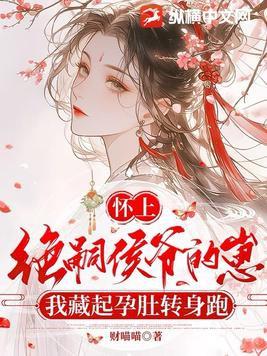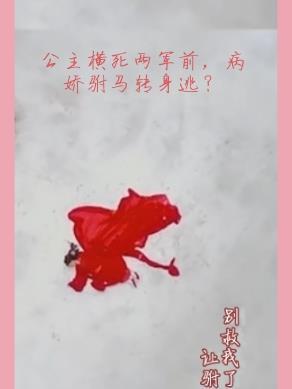紫夜小说>千秋宴是什么意思 > 第七十七章 不知我者(第2页)
第七十七章 不知我者(第2页)
三日後,陆忠的奏折传入漌水,一时惹朝野震动,南王立马召见陆忠进京。
一路上,陆忠瞧着路上的百姓,瞧着阁楼上品茗论辞的文人,瞧着挑着河鱼拉着小儿的鱼贩,不知为何,陆忠的眉头皱了一下。
迎着日光,陆忠下了马车,他坐在了一家寻常的茶馆里,点了一道膳食,名为红梅融雪。
大约是心里慌乱,他吃的很急,惹得店家奇怪,便调侃了他一句。
“又无要事在身,何必吃的这样急呢?”
陆忠看向店家,说道:“南国水草丰美,鱼游沸鼎,假若有一天,南国之水断了……”
店家耸了耸肩,笑道:“水岂会断呢?瞧你像个文士,说起话来却没头没脑的,你若是说天灾我信,说水断我却不信。”
陆忠摇了摇头,轻笑一声,说道:“是啊,水又岂会断?”
店家觉得他奇怪,也未再与他多做交谈,陆忠吃完了膳食,付了些钱,又继续上路去了。
行至漌水,陆忠下了马车,经宦者的引见,前往南王宫面见南王。
他走上石阶,行过大礼,才见殿内站满了文武官员。
“陆忠,依你折上所言,舟卿已归降仪国,再无转圜之机了?”
“不错。”
南王眼中闪过一丝愤懑,他看着陆忠,冷声问道:“那你上折,请朕向仪国拜玺称臣又是何意?身为我国百姓,岂能对奸贼俯首帖耳,言听计从?”
见状,卓岚笑道:“陛下所言,你可听清楚了?陆忠,眼下国之危难,你不思报国,反生异心,甘心做那逢迎谄媚的小人,你这般的人,究竟何来的脸面敢站在南王宫的大殿之上?”
“所谓‘忠’字,意在忠君丶忠国丶忠心,你不妨问问,你哪有一点对得起这个‘忠’字?”
陆忠拂了拂袖子,淡然说道:“相邦既说,我自然不敢不答,所谓忠君……”
他吸了口气,继续说道:“我国国力衰微,粮食匮乏,兵将不过十馀万,马不过万匹,车不过千架,以少胜多,以寡敌衆,是为愚行,如此大的差距,如此衰微的国力,是胜是败,一眼便知。”
“大人说我不忠,我不辩驳,眼下情景诸位皆心知肚明,何必装聋作哑?人如草木,民如基石,为君者固然在九天之上,享万千荣华,也应当心怀一颗仁心。”
“既是必败之局,又何必葬送数万将士的性命?”
“你这国贼,休要再言!”一将指着陆忠的鼻子怒骂。
“难不成你想凭借一张巧嘴,让我等皆沦为仪国的阶下囚,跨下臣吗?此奇耻大辱还是陆大人自己受着吧,我等宁可一死!”
陆忠挑了挑眉,说道:“让仪国的兵刃抵在你们的脖颈上?妻儿该如何?南国的百姓又该如何?你们依着所谓的气节,便要让南国的百姓与你们一同陪葬吗?”
殿内陷入寂静,过了很久,一名老臣上前一步,缓缓张了张口。
“你又怎知,百姓皆如你一般,甘心做那受辱之人?”
“除却性命,荣华,人这一生,所求的,所执着的,还有道义,还有气节………在旁国讨生活的滋味,你陆大人岂会明白?”
闻言,陆忠垂眸,却是笑了,他轻轻摇了摇头,说道:“我自然是不知的,我所知的,莫过于性命为大。”
“只是,此战到最後,所伤者,也不过是南国的数万将士,或依诸位大人之言,拼力一战,誓死不降,倒也不错,可…我却想问一句,放眼朝堂之中,可有一人能与仪国诸将一战?”
“是早已言败过的易将军,还是已屈服于仪国铁骑下的谷丶陈二位将军?于将军年事已高,就算出征又能捱到几时?还是说,靠着诸位的口舌,便能使邑桥的十万仪军尽数而退?”
话音未落,南王的神色已变。
片刻,他出言制止了陆忠,尽管卓岚拼命拦阻,南王依旧遣散了衆臣,并将陆忠传进了内殿。
一缕清香在两人中间飘散,陆忠站在那里,毫无波澜的诉说着。
不知过了多久,陆忠出了大殿,他走下石阶,在衆臣的注视下扬长而去。
一阵钟声响起,使得陆忠擡眼回望,他仔细的瞧了瞧,不知道为什麽,他忽然想起来方才在内殿他与南王的交谈。
残香之中,南王撑着额头,慢慢的从箱子里取出一卷竹简,他无力的笑了两声,说竹简是由尹世安所写。
说罢,他放下竹简,低声道:“可惜,朕如今……”
话没说完,他立马摆了摆手,恢复了往日的神情。
“朕这一生,想过东征西战,策马奔腾,时至今日,却越发的觉得难行,仪国君王…并非是个刁钻之人,想当年…想当年朕还与一同在山上闲游,他还指着朕宫里的壁画连连赞叹………朕亦知道,求降是唯一之策,可朕……”
南王的嘴角抽了一下,轻声说道:“可朕,就是有一点不甘心。”
“身为君王,肩负着万民的心愿,朕知道,朕对不起他们,朕也对不起相邦……”
“有时候,朕时常在梦里想,如果朕拿起弓,提着剑,带领着南国的子民讨伐仪国,让仪国的街巷里都流传着南国的故事,孩童们都歌唱南国的歌谣,该有多好……”
此时,屋外传来宦者通报,称卓相邦请见,南王的神情顿了一下,随即摆了摆手。
“陛下……”陆忠仿佛明白了什麽。
南王擡起眼帘,将竹简递给他,说道:“将此物作为信物,替朕送至仪军军营。”
“朕……还需些时日,撰写降…撰写文书。”
陆忠听的明白,他接过竹简,接着便退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