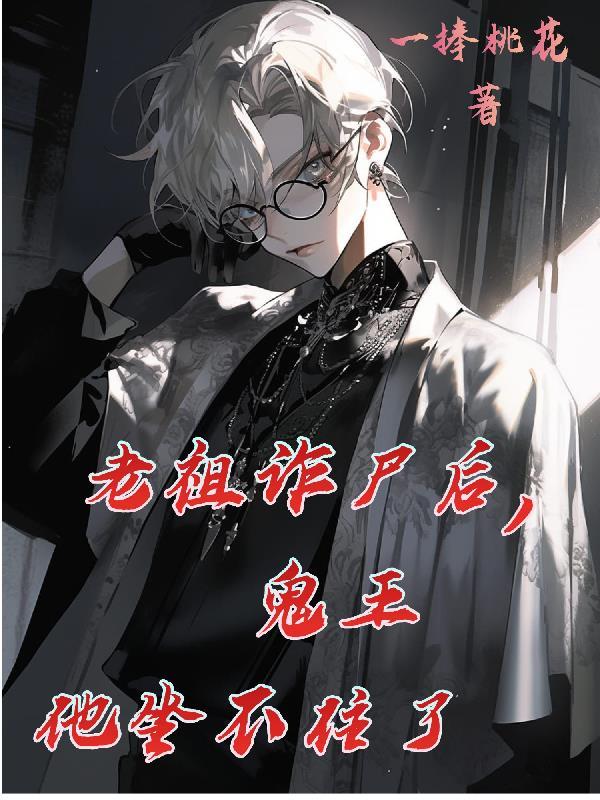紫夜小说>鎏金宝瓶是什么意思 > 第 40 章(第2页)
第 40 章(第2页)
林尔岚挑走汤里的香菜:“反正过了领证就当奖励,不过就当安慰怎麽样。”
毛小桃用力握着啤酒瓶:“没想到我毛小桃又能做伴娘了啊,哈哈哈哈!”
闫丽啃着一块羊蝎子:“你对做伴娘有什麽瘾吗?”
“可以抢捧花!”
闫丽说:“你提醒我了,我下次一定送花给你。”
毛小桃说:“不要,安慰奖有什麽意思。下次记得当秦奋的面这麽大声给我说。”
林尔岚说:“这一回看来我们402真的都是成了2的偶数,个个都成双了。”
可闫丽倒光了最後一点可乐,灌了一大口说:“可惜我要拖後腿了,我准备离婚了。赵晋鹏出轨了。”
捞光了羊蝎子的红汤锅咕嘟咕嘟沸腾着,只有一根煮黄了的香菜徒劳翻滚。
毛小桃拿了长筷子在里面捞了好几回,什麽也没捞到,又拿汤勺去捞,也没捞到。
她就靠地一拍筷子,滚烫的油星飞溅,染脏了红桌布,她顿时就骂起来。
我陪闫丽回家,支维安出差去了,赵晋鹏搬出家了。
我们又可以像大学时睡上下铺那样,秉烛夜谈了。可闫丽明显不太想说话。开了空调後,她恹恹地躺在床上,半天才把蚕丝被勾起来,遮住了脚脖子。
“夏天了开空调舒服,可容易脚凉。”她忽然说。
我知道她不是脚凉,是心凉。
我回忆起他们认识的最初,这一路我都见证过来的。他们婚礼前甚至还讨论过我是不是应该做媒人,而不是做伴娘。
我心里也跟这强劲的空调风吹过似的,哇凉哇凉。
“赵晋鹏真不是东西。”
刚才毛小桃一个劲在骂,林尔岚也愤愤说了两句。
我看闫丽一直不说话,只是带着看破什麽的笑。我觉得脑子很混乱,总觉得这两个人不应该是这样收场,所以我没多说。可到这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忍不住了。
“我当时真不该加他微信,加了也不该说你没男朋友。”
“这个故事从这个角度看是这样,他出差出轨了女同事,然後被老婆无意中发现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但还有另外一个角度。”闫丽说,“我只告诉你,你要不要听听看。”
闫丽的声音似乎真的从蚌壳中挤出,非常艰难。
“我们没有发生过任何实质性性关系。换句话说,这个婚姻有名无实。四年多来,他一直只有一个名义上的女朋友和妻子。”
空调出风口上有一条红带子,被吹得笔笔直,但有一点打颤。
我震惊得犹如这条笔直的红带子。
可闫丽微微笑着。仿佛早就知道这话告诉任何人,人家都会是这样的反应。
“我一直很害怕这件事,他说他能等,他可以慢慢等。我们也为这事吵过架,可他还是觉得要不我们先结婚,也许结婚了我没心理负担会好点。可我们试了又试,我还是害怕。我们开始为这件事吵得越来越多,到後来避而不谈。最後就这样了……”
经常肆无忌惮开车的闫丽竟然害怕性,这是为什麽。她看出了我的疑问,所以她自己说下去了。
“我小时候隔壁有个退休医生,人很慈祥,我们几个小孩子都常去他家玩,拿他们家的一次性针筒给月季花打针,翻出听诊器互相听听心脏。有一天,我一个人去了,那时候他老伴刚去世没多久。他说他帮我检查一下,我心脏是不是比其他小孩跳得有力……”
“我当时懵懵懂懂,不知道发生了什麽,後来还去他家玩了好几次。有时候他还会带我去巷子的小店买新出锅的生煎。那家生煎是有名的,皮煎得又薄又脆,金黄酥脆。坐在铺子里,他帮我拿好碗,倒好醋,我还帮他掰过好多次一次性筷子。一起等着生煎出锅,听着那油滋滋滋冒着,带着肉香气端上木桌。”
“後来上青春期教育课的时候,那个人已经死了。你不知道找谁去恨,只有每次闻到风里传来油炸食物的油气,我都会觉得恶心。我闻不了这样的味道,可是在床上,我经常会隐约闻到外面传来这样的味道。我就在会想谁家的厨房在煎东西呢,在做什麽样的一盆菜呢,是在煎生煎吗?是我们家的厨房吗?我就受不了,我一定要出去看看。”
我完全呆住了,同时我闻出身上沾染上的火锅气味里,似乎也有一种油气。闻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眼睛下很凉。
反而是闫丽拿了一把纸按在我脸上,跟我说:“很久的事了。”
我擦了擦眼泪,半晌我才说:“你有没有告诉过他?”
闫丽摇摇头:“开头一直想说,但说不出口。後来在反反复复的吵架中就越来越不想说。开始觉得可能早晚要完,那就不想要一个要走的人知道这件事。”
我拧着手中的纸,“那你为什麽会告诉我。”
“不知道。一起躺在这里,一起吹着空调。一切真的完了的时候,感觉说出来也无所谓了。而且晚饭时只有你没骂他,当你也开始骂他时,我忽然又为他难过。他是真心实意想过要等我的,我知道的,我看人没那麽差的。”
我把用过的餐巾纸揉成团,扔到床头,拉起蚕丝被盖住了自己的腿。
这种过分轻薄的被子,毫无重量,在空调里盖着半点也不暖和。
闫丽说:“早知道就不该开始,世界上恐怕也就我们这一对会没完没了为这件事吵架。”
“不是的。我们也会。”没想到曾经连暗恋都不愿意告诉舍友的我,有一天会跟舍友头并着头聊这样隐私的话题。“比如有时候吵架,他会想用这件事来解决问题,我会想解决完了问题才能做这件事,这时候就会吵架。”
“你以前不老说性也是彼此了解的途径。”我说,“你都不让他了解你,你们怎麽会有性呢。”
闫丽严严实实盖着被子,连一丝手脚都没露出来。
这被子很凉,但是够软。
我接着说,“你听不下去我骂他,可接下来他还被很多人骂,连程功和施烨都会骂他,如果他不是那种会为自己辩解的人的话。可你认识他这麽多年,你觉得他是那种会为自己辩解的人吗?”
闫丽望着空荡荡的天花板。
他们选了一张在草坪上贴脸而笑的照片放在床头,此刻这张合照正在床头对着我微笑。
“他不是。他会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我开头就不该对其他人说这种隐瞒了一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