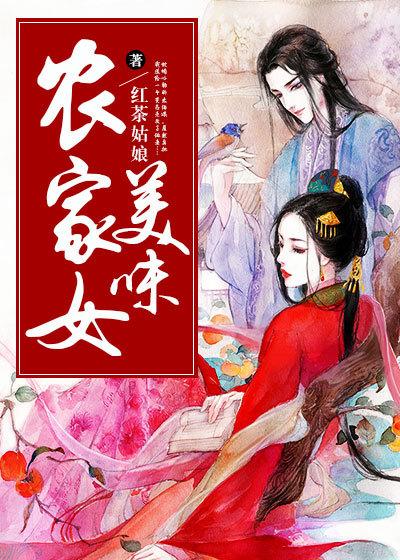紫夜小说>赶尸赴任免费阅读 > 第三章4(第3页)
第三章4(第3页)
***
从河间府出来後,祝鸿文的骡车上就多了个人——小舅子王守义。
有些事情,多个人,就不好办了。
更别说那王守义还像个牛皮糖,紧黏着祝鸿文不放。祝鸿文几次找机会想将人支开,均未成功。祝鸿文只得抓紧赶路,看能否在进了雄州县城後,想法子先安置了王守义,再想办法解决车舆里的麻烦。
紧赶慢赶,自东京出发後的第九日隅中巳时,祝鸿文终于到达雄州雄县县衙。
从石阶下往上望,是威风凛凛的一对石狮,石狮往上便是高挂红底金字的大匾,上书:雄县县衙。祝鸿文看着这四个金漆大字,心中激动不已,一时间竟想落泪。
千辛万苦入官门,从此不复为白身。
“姐夫,你以後就是这儿的主簿了!”一路跟着的王守义甚至比祝鸿文还要激动。
“你在这等我。”
祝鸿文收拾好心情。踏上石阶,走向辕门,向那守门的防送公人递上官凭腰牌,“鄙人祝鸿文,乃新任雄县主簿,此来上任。”
那公人擡眼看了祝鸿文,接过那官凭腰牌,虽不识字,但好歹看懂了那红色大印,。
那公人一揖:“官人请在此处稍等片刻。”偏头和边上公人眼神一对,边上那公人立刻便拿着祝鸿文的官凭小跑进了衙门。
祝鸿文也一揖:“有劳。”
不多时,出来个身着圆领公服的人吏,仔细对了祝鸿文与那官凭腰牌上的面貌,似看到救星一般:“是你,咱县新来的主簿!”
祝鸿文一揖,“鄙人祝鸿文,正是…”
“官人您可来的太巧了!”那人吏扶拉着祝鸿文就往衙门外赶。也不知何时,衙门外居然已停了辆马车,人吏将祝鸿文推上车舆,“州府衙门那儿正要商议如何追查榷场走私,县尊身体不适,正好您负责这块儿,需得赶紧前去。”
“可是我骡子…还有我这身衣服…”祝鸿文为难道,“衙门与会,我总不能就穿这套常服去。”
“衣服,对,衣服得换!”那人吏又拉着祝鸿文往衙门里跑。
“等等。我还有家眷…”祝鸿文指着王守义。
那人吏这才看到後面的王守义,也不寒暄,朝後头那公人吼,“快啊,快带主簿和家眷进内院!”随即又转头笑道,“官人,我去给您拿官服,您要动作快点儿。”
祝鸿文牵了骡车,跟着公人绕到衙门侧门。
不知怎地,他心口急跳,总觉得似有哪里不对劲。
“姐夫,你咋了?”王守义发现了祝鸿文的异常。
祝鸿文看了眼身後车舆:“没什麽。”
很快,主簿厅到了。
“官人,这是主簿厅,您往後起居办公都在这儿…”那公人介绍说着,“骡子我给您牵去马槽养着。”
“不用。你去外头等我。”
待公人走後,顾不得王守义还在边上,祝鸿文来到车舆前上手一摸,老铜锁是扣着的。
可他悬着的心还是没放下,毫不犹豫地打开了老铜锁。
门一开,王守义先惊了,这…是什麽?
“姐夫,你运这石头作甚…”
车里的雕花木箱,连带着那尸体一并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半人高的大石头。
“你那箱子呢?”王守义很是奇怪,毕竟对那箱子姐夫可是一路宝贝得紧。
祝鸿文脑袋嗡嗡,全身发凉,压根听不清王守义说了什麽,只盯着眼前巨石极力回想。
什麽时候?到底是什麽时候没了?
河间府出发,他还查过一次,那时箱子和尸体都还在车上。
为防王守义乱翻,河间府之後,他可是连睡觉都靠在车上。
…
除了昨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