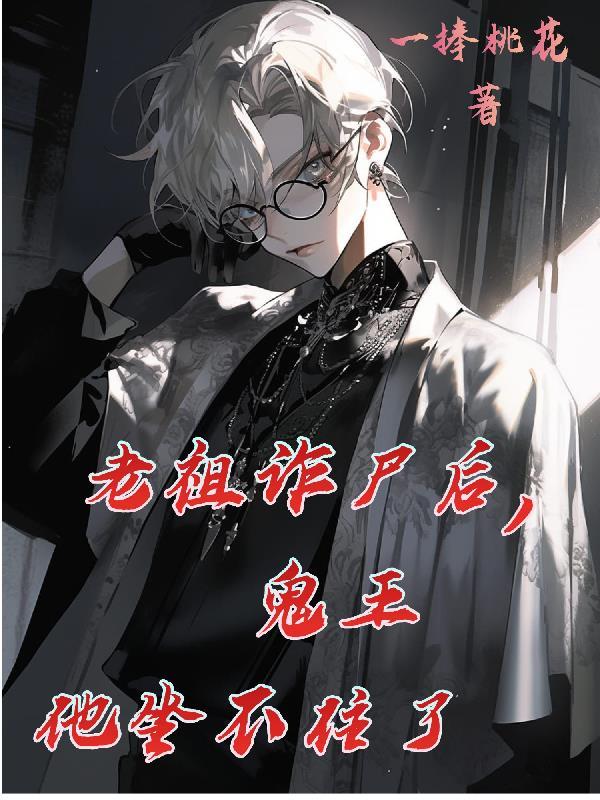紫夜小说>重生后她真成了祖宗 > 青衣客把酒浅笑纡筹策并进奇谋(第1页)
青衣客把酒浅笑纡筹策并进奇谋(第1页)
青衣客把酒浅笑,纡筹策并进奇谋
夜幕时分。
九州·京城。
皇城下,一名容貌不俗手持长剑的青衣女子,三指托尖儿端着茶盏,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抿着嘴唇,似乎是在思量着什麽很要紧的事情。
倘若实在是在太平盛世下,像这样一身江湖打扮的美貌女子走在街上,不免会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但在如今这人鬼不分的乱世江湖之中,谁还有哪个闲情逸致管别人怎麽样呢。
“决战万鬼之祖·祪嫣祭世之期不日将至,而如今最好的帮手莫过于此人。”那青衣女子端着茶盏抿了两口,眼神又一次望向了皇城,仿佛想要说些什麽,却又突然变得沉默,“这座皇城里的那座皇位是多少人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东西,但这些人争来争去又能怎样呢?无非黄粱一梦,醉生梦死罢了。李从云此人虽然一向也是野心勃勃,但和这些人比起来,却又似乎不太相同。
其人性狂而自傲,善谋而叛道,刚愎自用,不合于衆。倘能加以利用,必有事外之功。但我该如何说服他呢?
诛剿万鬼之祖·祪嫣祭世无论人间,尤其是现今中原不管由谁做主,都必须抓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三界之中打出威望气势,往後无论三界中的神佛妖魔自然都不敢再蔑视人间。
那麽,此役过後,人间便也能在三界中拥有一定地位,绝不至于像从前一样任由妖魔作恶,神魔看轻,备受欺凌,鲜有抗争。”
青衣女子一边琢磨,一边凝望着皇城高墙,“怎麽办呢?想来想去,还是没什麽好法子。既然想不出什麽法子来,那不如就还按老规矩办。今夜,大闹京城名震天下的楚侠女就要再闹京城咯!”
青衣女子心里打定了主意,不禁感到一阵放松,“小二,再来两坛好酒,另外小菜也要两份儿,一份儿豆腐烤串儿,再来一份儿油炸花生。”
时至深夜,行将入梦。
皇城之上,锦衣夜行。
青衣女子手持长剑背靠着一堵院墙已经在皇城外,不远处的一个小巷子里等了约摸两个时辰了。
“差不多了!我也该去朝觐一下这位老朋友了。”
青衣女子仗剑转身,面朝皇城,浅浅一笑,缓缓走来。
冥界·辛夷山庄。
弗遇风亭。
三日之前那个夜晚。
韩让咬破手指,将他一直秘密储藏在自己心窍之内的夸父鹿血取出,倒入其所特制的阳泉酒调制出来的一杯鹿血酒,缓缓灌入落什心儿口中让她喝了以後,才终于让韩让为落什心儿悬着的那颗心放下了些。
“这杯酒喝完了以後,你应该很快就能没事了。”韩让爱不释手地轻抚着落什心儿的眉眼鼻翼脸颊,心底仿佛有难以细数的绵绵情愫不断涌出,这种感觉让他不禁为之眷恋而又为之哀愁,“落什心儿,你知道我当初救的那只小鹿为什麽如此重要和特别吗?因为那只小鹿它呀,可不是普通的灵鹿,而是当初夸父追日的时候,一直偷偷跟在夸父後面追随了很久的一只火麟神鹿。
当时它似乎才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我恰好路过那儿,便说它如果愿意,我可以帮忙救它出去。在我救了它之後,它为了回报我就给了我几滴它所独有的鹿血,并说它的这几滴鹿血可以有很大的益处。,只是普通人恐怕无法承受。
而且,让我更为诧异的是,它竟然说我的心窍与常人不同,似乎长得好像一颗大树的树根一样,而且还散发着一丝丝似有若无的诡异阴气,只是寻常很少有人能闻到,只有火麟神鹿这样的天生神兽才能闻得出来。
那时候听到火麟神鹿把这个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告诉我的时候,我几乎想要把自己身体里这颗‘心’直接挖出来一把烧掉算了。
但火麟神鹿却又告诉我说,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向我提议赠给我的那几滴鹿血,并且还要我就将那几滴鹿血储藏在我心窍之内。我本来还有些害怕,想要拒绝。但突然想到你好像很喜欢吃鹿肉,于是我就在火麟神鹿的帮助下,听从它的建议,将那几滴鹿血放在我心窍之内,一直为你保留着,想着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没找到最後果然还是用上了。”
韩让说完,黯然一笑,“你说,这该说是冥冥之中的天意,还是皇天不负有心人?”
此时。
天上却突然聚集起一片浓稠血云,夜空深处一个传来了几分清荡幽寂,温柔妩媚,又夹杂着一丝隐忍低沉,幽怨凄迷的,女人的声音,“好久不见,飞鸟先生。哟,这是谁的姑娘就这麽躺在一个陌生男子的身边,难道就不怕有人见色起意图谋不轨吗?
但话又说回来,现在在飞鸟先生旁边被飞鸟先生如此心疼着的人,为什麽就不能是我?我冀云烟到底有哪一点儿,竟然还不如这麽一个随便没规矩的女子能讨飞鸟先生的欢心呢?呵呵,我这麽说她,飞鸟先生该不会生我的气吧?
那我可得十分十分得伤心咯,可伤心不重要,重要的是飞鸟先生是否还记得咱们之间曾有过的约定呢?如果飞鸟先生要是打算食言的话,那云烟可就真要伤心了!惹怒我的下场,相信飞鸟先生也是很清楚的吧?!”
“废话说了那麽多,有点儿用的,也就最後这一句,这可不像你呀!”韩让端着酒杯喝了一口,似乎还暗暗叹了口气,但却只眨了眨眼睛,连头都没往上擡一下。
“飞鸟先生说笑了,我冀云烟看起来很像凶神恶煞吗?如果飞鸟先生实在是不喜欢别人在你面前提及,你和那位落什心儿姑娘之间的事情,那我倒也不介意和你说一点儿别的事情。比如说,你我之间的那个秘密约定,如何呢?”冀云烟道。
韩让摇头晃酒,冷冷一笑,“约定?如果那也能算是什麽约定的话,那这世界上但凡是掌握了某种物质,抑或是拥有了某种力量的人,这些人是不是都可以仅凭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就和任何人订立什麽所谓的‘约定’?倘若如此,那这世界公理何在?道义何存?这种所谓的‘约定’又何需敬畏?何需遵守?”
“哦?那听你这话里的意思,你是想要不认账咯,是吗?”冀云烟。
“哈,我若不认账,你又能奈我何?”韩让。
“呵呵,韩让,我突然发觉你好像变了。当初,在斋戒城的时候,你可不是这麽说的,因为那时候的你,绝不可能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那究竟是什麽让你改变了呢?我想,应该就是这个女人吧,是吗?”冀云烟冷笑道。
“你敢动她试试?”韩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