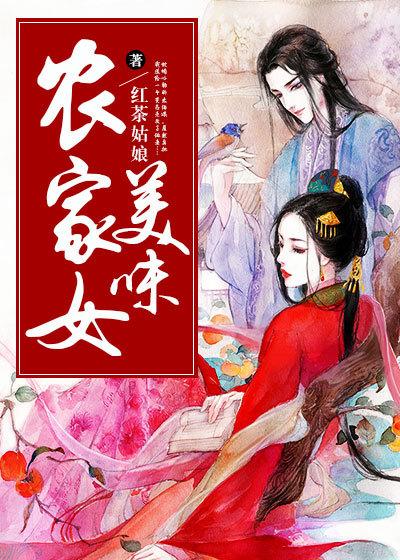紫夜小说>我尽有苍绿 > 你我这美梦(第4页)
你我这美梦(第4页)
阮秋季起身,很想扭头走了,如棠看着他。阮秋季心道,只有商柘希能受得了他这脾气,嘴上说:“我打个电话,回来再谈。”三分钟之後,阮秋季回来了,如棠还坐在那儿,有些落寞地看窗外,阮秋季坐回来,跟着瞥了一眼外面,冬天的街景光秃秃的,什麽也没有,连片叶子都没有。
“如果你真想那麽做,我们要仔细规划一下。我在佛罗伦萨那边有朋友,如果事情成了,你可以在那边念书丶正常生活,但那样算是外逃——你不能回国了。虽然商柘希能恢复人身自由,但会被限制离境,出不了国去看你,你们只能等,等哪一天有了转圜的馀地,而他也有能力去看你,或者把你弄回来。”
如棠一个字一个字听完了,说:“这是最好的办法。”
“目前看来是的,这样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也可以接管江山了。但我无法保证你们要等上几年,我要劝你一句,人是经受不住时间考验的,如果是我,绝对不会等任何一个人。”
“我可以等。”
“你相信他吗?”
“我相信。”
阮秋季无言,如棠回答得太果决了。过一会儿,阮秋季说:“你相信他,却不肯告诉他?或者说服他同意?”
“他一定会自责,伤心,他现在的处境够艰难了,他会钻牛角尖,想不开……我绝不会让他坐牢的,那等于杀了他一次,我要他好好的,完好无损回家。”
“你可以接受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吗?”
“我……一个人也可以活下去,也可以照顾好自己。”
那个眼神太勇毅。
阮秋季又是无言,最後只有一句,“好。等我的消息吧。”
日记写到了第二十页,每一天商柘希醒来,打开日记本写点什麽才能开始新的一天。
暑假漫长,如棠每天在外婆的监控下,打电话也要偷偷的。“7月20日,如棠打来电话,跟表哥的朋友一起坐过山车,吃糖水。”商柘希不是情感多麽外露的人,写日记也不愿暴露自己,他只是太无聊了,所以也用无聊的口吻记下小事。
如棠是从糖水店里打来的,声音听起来偷偷摸摸,做贼一样紧张,“喂,哥哥,你在家吗?”商柘希坐在客厅,拿着听筒很想笑,他不在家怎麽接电话呢。如棠又说,表哥有好多朋友,带着他一起出门玩。
他们去了游乐园,一个姓莫的哄他叫哥哥,但他就不叫。
“你吃了什麽?”
“我吃了……”
可能因为年纪小,排了很长的队,吃了芋圆,看了一本喜欢的书,冰激凌化得太快,教他钢琴的老师很凶,这些小事也要拿来说,像七点钟的新闻一样,一条接一条郑重地播报给对方。
如棠刚上六年级,扎着丸子头,也还没吧台高,收银台的阿姨弯身看他,原来人还没走,还抱着听筒在说话,十五分钟了还没打完,眼睛滴溜溜地转,像一个间谍在观察表哥的朋友们。
莫连成走过来说:“小孩,你跟谁打电话呢?还没打完。”
如棠吸了一口气,压低声音说:“完了,他们发现我们了。”又宁死不屈地对莫连成说:“我不告诉你。”
“拜拜,我先挂了。”
商柘希把听筒贴得更近一点,但并不能让如棠的声音更清晰。电话里有小店的音乐,也有纷杂的人声,让如棠的告别听起来也很遥远。
他没来得及说什麽,而挂断的嘟嘟声是确切的。
“8月20日,没有打电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陪另一个人一辈子,就算是亲人也不例外。”
商柘希写下一行字,又觉得这样是很没出息的,很动感情的。暑假要结束了,窗外的蝉声还是很吵,他拿出小刀,一刀又一刀划烂日记本上的字,直到划烂到看不清,桌子上都是白色纸屑,人还端坐在桌子前。
原来人就算被抽光了灵魂,见不到依赖的人,麻木地学习工作,也还是不得不开始新的一天。就算连日记都没得写,不知道外面的天地变成什麽样子,新的一天仍旧会跟着指针往前拨动丶开啓。
商柘希并不是感到被抛弃,他只是觉得……那太孤独了。他有的,只是手心一张小巧的便签纸,上面写了爱人对他发出的誓言。他为了克服那样的孤独,也曾寻欢作乐,自我放逐,睡在不同女人的床上会让他好过一点吗,装作自己也被爱,也被很多人放在眼里,放在心上会让他好过一点吗,玩弄别人的心,用来填补自己对如棠的嫉妒,会让他好过一点吗,美丽的事物总有一天会逝去,而他短暂拥有过了体验过了,会让他好过一点吗,人总会崩溃,而他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崩溃中,认清现实会让他好过一点吗,人应该维持体面,当他穿上西装,戴上名表,享受那份光鲜的优越会让他好过一点吗。
商柘希说不清了。
那天他走下台阶,雪花落在脖颈上是很轻的,融化的冷感转瞬即逝,仿佛那就是爱,渺小的爱。可雪花不是一片一片,从门口到车子的距离,有无数片,无数的爱,雪花像如棠的目光,钻进了他的头发,他的脖子,还有衣领下他的後背。
雪地到後视镜的距离,也有雪山崩塌。
冻裂了他的心。
门终于开了。
但这一次来的不是律师,也不是检察官,酒店房间一览无馀,商柘希一回头,就看到阮秋季站在门口,微微点头示意。阮秋季主动说:“好久不见。”
“有什麽事?”
“恭喜,你自由了。”
那声音带点不太清晰,也意味不明的客气。
商柘希回到了家,什麽都没有变,还跟一个多月前一样,除了新年新贴的福字,添了一抹喜庆的红。文姐和厨娘回家了,做了他爱吃的饭,司机也开车来接他们,接过商柘希手里的小行李箱,那是如棠之前让律师帮忙送的换洗衣物。
就跟梦一样。
阮秋季没怎麽说话,有种异样的沉默。商柘希站在客厅,还在等,等这依稀未变的场景里还有个未变的人。天气好,地板新抛了蜡,阳光照进来,光泽十分漂亮。进门之後,短短的一分钟,这栋房子都是安静而温馨的。
没有人像往常一样走下楼,没有足音。
商柘希忽然意识到了什麽,视线晃动,回头看向阮秋季,说:“如棠呢?”
阮秋季也看着他,平静回答:“他在去佛罗伦萨的飞机上。”
商柘希没听懂他在说什麽,过了好一会儿,在两个人紧迫的对视中,他好像才终于懂了,但紧接而来的还有深深的愤怒与绝望,商柘希两步上前,一把拽住了阮秋季的衣领,阮秋季也被迫反抓住了他的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