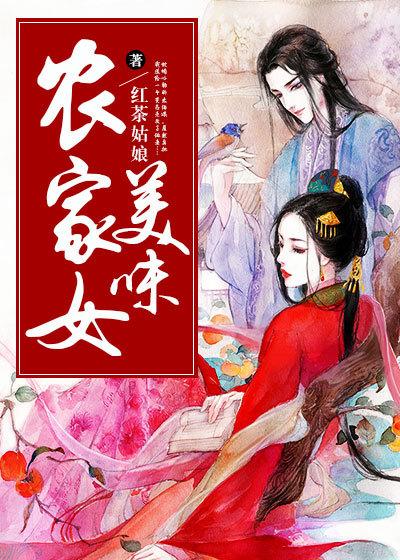紫夜小说>檀奴简介 > 第 10 章(第2页)
第 10 章(第2页)
已经答应的三百万两白银还不够,这太子是一定要大盛下去趟这趟浑水。
“太子生性残忍,阴晴不定,清宁没有说错什麽话吧?”
这些雀铭都没在场,但是清宁一向温和有礼,即便是太子故意为难恐怕也挑不出错处来。
“大小姐有礼有节,太子说不出什麽。”
但是想起今日她在船中突然焦躁难安的样子,他也不明白那时她到底为什麽不愿下船。
难道是不想见太子?如此倒也合理,太子本就看不惯越家,自然也不会给她好脸色。
当时他也跟下去就好了,跟在她身边至少能知道她有没有被为难,只是她最近愈发讨厌他的脸,甚至头一次命令他去捡水中帷帽,想来是不想他在衆人面前出现。
想到这,他表情难安,神色愈发暗淡下去。
越尚书又问了两句,瞧他今日脸色惨白,似乎不太对劲便放他回去休息。
“还有六个月,到冬日时候我想个法子送你往洛阳去,到那里也不可懈怠,我能帮你的已经没有多少,到时候全凭你自己。”
“贪冗沉珂正待改换,形势已然刻不容缓!我今年曾请滕大人往凉州调查,他说那边情况很不好,你现在才出仕已经有些晚了,换个身份快些到我身边来,现在朝廷内急需有才有识之人动一动这瘫痪庞杂的官场。”
他学了这麽多年为的就是改一改这朝廷的毛病,让行走在阴云下的百姓有条活路可走。
雀铭沉沉道了声是。
越尚书想了又想,一句话在嘴中已经存了好几年,此刻临到终了不免再次勾起念头。
“自此一去如渡火海,明知不可为,我却还叫你来朝中,雀铭,其实若是你……”
他猛地提声打断老师,“明知不可为的事除了我别无他人能坚持下去,老师明白的,为国为民兼济苍生,雀铭无悔!”
越尚书看着他的样子一时动容,又仿佛看到了当年恩师的影子。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君子之行,羽衣昱扬。
若是人人都想的在这种世道下独善其身,恐怕这国这家顷刻就会化为烟尘。
雀铭拜别刚要出去,越尚书这时又想起什麽忙拦住他。
“从现在开始还是不要再陪清宁出去了,正是关键时候,别再出什麽差错。”
雀铭一愣,赶紧说。
“现在变动反倒叫家中下人起疑,况且小姐也不会答应,到时候更不好找理由骗她,还是保持原状的好。”
越尚书一听倒也是这个道理,于是叫他勿要改动,随即放他回去休息。
雀铭提着灯再次从小路回到马棚,简单将活计做完回了房间。
躺在床上只感觉今日鼻子闷闷的有些不适,他一想,果然是下水之後穿着湿衣服太久,此刻可能染了些寒意。
今日大小姐也是,她从上船开始就不太对劲,到後来甚至迷迷糊糊的昏睡了一阵。
他想起抱着她上车前她说的话。
“你有没有看到我为你写的……”
写的什麽呢?
大小姐喜好诗词,自己也常常写些东西,可从没听到她为谁写过东西,她说的“你”是不是自己呢?或许是迷糊间把他当成了别人。
毕竟自己在她眼里应该就是个下人才对,还是个她瞧不上的下人……
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在被子里又转了个身朝向内侧,眼前灰墙逐渐变得深邃,像是一面镜子将他吸了进去。
她说的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他,即便是,恐怕也不是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