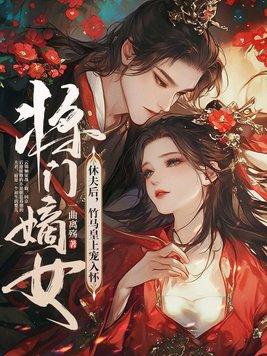紫夜小说>springer nature > 相握(第1页)
相握(第1页)
相握
自那天走廊的意外之後,我的世界仿佛被重新校准了中心。
那个叫做周禹的少年,像一颗突然闯入我平静星系的恒星,带着不容忽视的光和热,吸引着我所有的注意力。
开学第一周,对于高中生活的新鲜感和笨拙探索还弥漫在空气中。
我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寻找一切可能看到周禹的机会。
课间操时,我的目光总能精准地落在三班队伍里那个熟悉的身影上;中午食堂人头攒动,我端着餐盘,眼神却像装了雷达,扫视着每一个角落,只为了能“偶遇”他,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一眼他低头吃饭的样子。
这种小心翼翼的注视持续了几天,直到第二次真正的交谈发生。
那是在图书馆。我去借一本老师推荐的拓展读物,在文学区的书架间,我又看到了周禹。他正踮着脚,试图拿取书架最高层的一本书,指尖几次堪堪碰到书脊,却总是差一点。
心脏又开始不争气地加速。
我深吸一口气,走过去。“需要帮忙吗?”我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静自然。
周禹闻声回头,看到是我,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喜:“张宸之?好巧呀。嗯…就是那本,《瓦尔登湖》。”我身高有些优势,但也不算轻松地帮他取了下来,递给他。
“谢谢!”周禹接过书,笑容绽开,“你也来看书?”“嗯,来借本参考书。”
我晃了晃手里那本枯燥的数学题集,心里暗自庆幸自己不是空手而来,显得目的性没那麽强。
“《瓦尔登湖》,”我找着话题,“你喜欢这种类型的书?”
“嗯,语文老师推荐的嘛,”周禹笑了笑,手指轻轻抚过书封,“不过也挺好奇的,想看看一个人住在湖边树林里是什麽感觉。”
就着这个话题,两人很自然地并肩走到阅览区坐下,低声交谈起来。从《瓦尔登湖》聊到喜欢的作家,从语文老师的严厉聊到初中看过的闲书。
我发现,和周禹聊天是件极其舒服的事情。他思维敏锐,总能接住我的话头,偶尔抛出一些有趣而独特的观点,眼神亮亮的,带着一种对世界真诚的好奇。
他说话时习惯微微偏着头,很认真地听着,让我感觉自己的每一句话都被郑重对待。
那次图书馆的交谈像是一把钥匙,轻轻打开了两人之间那扇陌生的门。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的“偶遇”似乎真的频繁了起来,或者说,因为彼此都有了留意,相遇才变得顺理成章。
我们会开始在走廊碰面时,不再是仓促地点头说“嗨”,而是会停下来简短地聊几句今天老师的拖堂或者难解的数学题。
周禹知道了我初中是在另一所中学读的,知道了我喜欢画画。
我也知道了他有点怕体育课的跑步测试。
周禹也会告诉我,自己从小喜欢写小作文,梦想是以後能学文学类。
我听得很认真,说:“不会啊,感觉很厉害……”杂杂碎碎的乱吐一通。
青春期的感情,常常伴随着强烈的分享欲。
我甚至开始每天期待上学,因为学校里有周禹。
我会把早上路上看到的有趣事情记下来,想着课间能不能说给他听;我会格外努力地学习,尤其是物理,因为那次意外的触碰,也因为希望能在他问起问题时,自己能给出清晰漂亮的解答。
一周後,周五的下午,放学铃声格外悦耳。我正收拾书包,同桌兼好哥们邱霭明用胳膊肘碰了碰我,挤眉弄眼地示意窗外。
我擡头,心跳猛地停了一拍——周禹正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而与他并肩的是隔壁班的一个女同学。
在几个男生起哄般的低笑声中,我几乎是蹑手蹑脚的摸了出去。
“张宸之,等等。”是老班的声音,他是一个稍胖的中年男子,眼神总是真挚而慈祥的。
他言简意赅的给我交代了黑板报的事,周禹作为语文课代表,老班让他留下来负责兼写文案。
“当然可以!”我答应得飞快,生怕晚一秒。
周禹低头和那个女生说了什麽,向我走来。那个女同学转身离开了。
不多时,空荡荡的三班教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夕阳透过干净的玻璃窗,将教室切割成明暗交织的方块。粉笔灰在光柱中轻轻飞舞。
周禹负责用尺子打格子和书写工整的楷体字,我则在一旁调着颜料,用彩色粉笔勾勒出迷彩图案和花草边框。
我们离得很近,近到我能清晰地闻到他干净的校服上淡淡的茉莉清香,能听到他偶尔因为写错一笔而发出轻轻的丶懊恼的鼻音。
我们时而低声商量着布局,时而因为某个滑稽的图案笑出声。
安静的教室里,粉笔划过黑板的沙沙声,和彼此轻微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静谧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