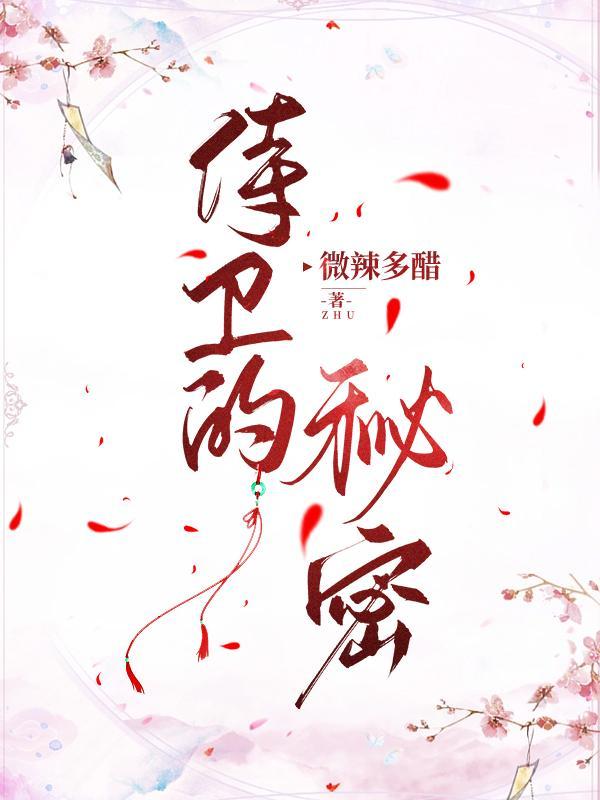紫夜小说>springer nature > 隔阂(第2页)
隔阂(第2页)
这里到处都是和我一样痴迷艺术丶个性鲜明的同类。画室里永远弥漫着松节油和颜料的气息,作品评论课上思想激烈碰撞,教授们的指点让我豁然开朗。
我的世界是斑斓的色彩丶自由的线条和无尽的可能性。我住在一个混宿的宿舍,室友有学雕塑的丶学设计的,晚上常常一起熬夜做作品,聊艺术聊人生,激情澎湃。
我几乎每天都会给周禹发信息,分享我的新画丶有趣的课堂丶奇葩的室友,还有校园里好看的角落,字里行间充满了兴奋和活力。
而周禹,则一头扎进了另一个世界。
顶尖学府的金融系,汇聚了最聪明的头脑和最强烈的野心。课程难度极大,微积分丶宏观微观经济学丶会计学原理……那些冰冷的数字丶复杂的模型和高效运转的逻辑,与他感性细腻的内心格格不入。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吃力,周围似乎每个人都能轻松理解那些他需要花费数倍时间才能勉强消化的知识。他很少再有时间看书,笔记本上不再是摘抄的美文诗句,而是密密麻麻的公式和图表。
他的室友们目标明确,讨论的是实习丶GPA丶和未来进入哪家投行券商。周禹穿着简单的T恤裤子穿梭在一群早早开始穿着西装套裙的同学中间,感到一丝难以融入的隔阂。
他开始强迫自己适应这种快节奏和高强度,像海绵一样吸收那些枯燥的知识,因为他没有退路。这是他自已选择的丶“现实”的道路。
他也会给我发信息,但内容渐渐变成了“今天经济学好难”丶“又要小组讨论,好累”丶“周末可能要泡图书馆了”。
我的回复总是试图充满鼓励,但我无法真正体会他面对那些天书般公式时的焦头烂额,正如他也越来越难理解我作品中那些“情感的迸发”和“形式的探索”。
我有点後悔了。
第一次约定见面,是在开学一个月後。两人都期待了很久。
我提前查好了漫长的地铁路线,倒了三次地铁,花了将近两个半小时,才终于站在周禹的校门口。
周禹早早等在那里,看到我,眼睛一亮,飞奔过来。
短暂的拥抱後,我兴奋地想拉他去吃好吃的,却看到周禹从书包里拿出了笔记本电脑。
“对不起啊张宸之,”他脸上带着歉意,“我们小组有个金融模型的作业下午就要交了,还有点收尾工作,我得先去图书馆弄一下,很快的!半小时就好!”
我眼中的光暗似乎淡了一下,但立刻笑着说:“没事,我陪你去图书馆。你弄你的,我画会儿速写。”
在安静的图书馆,周禹眉头紧锁地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手指飞快地敲击键盘。
我坐在他对面,打开速写本,却久久没有下笔。我看着他专注而疲惫的侧脸,感觉他和高中时那个在阳光下笑着聊《瓦尔登湖》的少年,似乎有哪里不一样了。他周身笼罩着一种紧张的丶被无形压力驱使着的焦虑感。
原本计划的浪漫约会,最後变成了陪他在图书馆赶作业,然後在食堂匆匆吃了顿饭。
分别时,周禹满怀愧疚:“下次!下次我一定把所有事都做完再见面”
我摸摸周禹的头:“傻瓜,没关系。学习重要。况且和你在一起待一会儿,我就知足了。”
但我独自踏上漫长归程时,看着地铁窗外飞速掠过的丶北京的繁华与陌生,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异校”这两个字背後沉重的含义。
它不仅仅是地理的距离,更是生活节奏丶关注焦点乃至整个世界的渐行渐远。
这样的见面模式,在後来的几个月里重复上演。
不是他被突然的讲座丶小组讨论拖住,就是他因为要布展丶赶作品而无法离校。即便见了面,共同话题似乎也在减少。他兴致勃勃地讲起行为艺术,他听得云里雾里;他抱怨债券市场波动,我也完全无法接话。
沉默开始时不时地出现在两人之间。
电话和视频的次数也在减少。常常是我晚上画完画发信息过去,他很久才回一句:“刚自习完,好累,先睡了。”而他早上起床,看到他凌晨发来的“才弄完模型,崩溃”的消息,心疼却又无力。
北京的秋天很短,冬天来得迅猛而干燥。
寒风凛冽,像刀子一样。
一个周六,我熬通宵终于完成了一个大作业,满心期待第二天和周禹的约会。他却打来电话,声音带着哭腔:“张宸之,对不起……周日不能去找你了。微观经济学期中考我没考好,教授推荐了一个很难进的学霸学习小组,他们周日早上有讨论会,我……我不能错过……”
电话那头,我少有的沉默了。
长时间的疲惫和一次次期待落空的委屈,在这一刻达到了顶点。我听着电话那头他小心翼翼的丶充满愧疚的呼吸声,看着窗外灰蒙蒙的丶陌生的北京天空,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席卷了他。
我第一次没有立刻说出“没关系”。
电话两端,是长久的丶令人窒息的沉默。
只有电流的微弱杂音,提醒着彼此的存在,却也凸显了那份横亘在我们之间丶越来越宽的鸿沟。
“不应该是这样的……明明我们已经苦了好多年,为什麽……”
夜色静悄悄,无人在意落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