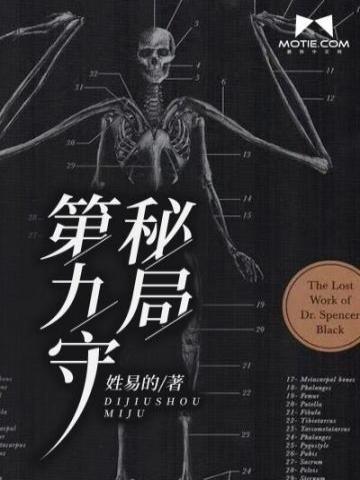紫夜小说>吉星高照对联 > 第三部分 1(第1页)
第三部分 1(第1页)
第三部分吉星高照1
车轮轧过减震带,挂饰摇晃,叮当作响。庄晓蝶动了动腿,回头看了眼後车座。小孩趴在座椅上,手上还抓着吃了一半的巧克力面包,已经睡着了。车里空气沉闷,充斥巧克力面包甜腻的苦香。庄晓蝶喝了口咖啡,往车窗一瞥,迅速倒退的幢幢黑影里显出年锦思模糊的脸。对方沉着脸,显然仍对她硬带上这小孩的选择不满。
已经到後半夜,路上车辆寥寥,她们驶进休息站,越过两旁黑沉的货车,选了最边角的位置停下。俩人简单吃了点东西,靠在椅背上休息。
手机关了机,也不知道廖老头看到车的凹陷有什麽想法,庄晓蝶在驾驶座上留了修车费——年锦思掏的。只跟了几天工,不告而别应当也没什麽问题。想是这样想。庄晓蝶睡不着,下车。那根烟还揣在兜里,先前她把它放挡风玻璃下,希望能用阳光晒干。确实干了大半,中心剩一点点潮意,但不碍事。
庄晓蝶拉开後车门,就见小孩书包掉下来,撒得座椅下到处都是。带小孩走的时候,小孩自己收拾了很多东西,背了个小书包。俩大人都没过问他装了什麽——实际上是不关心。现在看,包里除了衣服裤子,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东西。庄晓蝶先把毯子盖小孩身上,再拾起书包,将东西草草装进去了事。关上车门时感觉脚底下踩到什麽,硬壳,像个线圈绘画本,已经被她踩了好几脚,全是灰印子。庄晓蝶捡起来,拍了两下,翻过来检查,几张微笑的面孔在微弱的路灯下闪光,原来是本小相册子。这年头全是电子照片横行,极少看到冲洗成印的照片。
庄晓蝶看了看孩子——还在睡。她关上车门,点燃烟,慢慢踱步到路灯下,呼出一口烟。扉页写“但愿人长久”,字迹娟秀。
第一页只有一张彩照,微微泛黄,衣着朴素的小女孩小男孩及一个中年女人,均微微笑着,脸庞弧度类似,看起来是一家子。男孩比女孩高半个头,大概是哥哥。下面写了个日期,庄晓蝶稍稍计算,发现照片里的人似乎只比自己大三四岁。接着继续是这一家子的照片,从小学到大学,每年一张,中年女人头发逐渐花白,人越来越憔悴。到几年前的合照,只剩俩兄妹站在一棵树下。
再翻,就是一张婴儿照。後面都是小孩的照片,以及女人和小孩的照片,有一张男人的独照,飞蛾撞击路灯,落下慌乱的影子,烟灰落在那人脸上,庄晓蝶迅速抹掉,认出是小孩的父亲。手指立即捏住照片边角,犹豫是否抽出来撕碎扔掉,甚至烧毁。片刻後她继续往後翻,依旧只是女人和小孩的照片。
她翻回男人独照,飞蛾数次撞击,坠下来,啪地落在她脚边,翅膀挣扎扑扇。庄晓蝶後退一步,蹙着眉吸烟。邻居说女人得了不治之症,在小孩七岁时去世了。
徒劳无功。庄晓蝶心底默念,徒劳无功。带着这孩子,能走到哪?到明天年锦思必会提议丢下他。她们没法照顾这个孩子。只是一时冲动,甚至算不上善心。她不觉得带走这个孩子是善心发作。从跟邻居的交流来看,把孩子带走无疑是正确选择——避免邻居因没收到钱起疑心。她不想有人找这个男人。仅此而已。
但是孩子怎麽处理?
孩子怎麽处理?
烟吸到末尾,星点几乎亮在眼前,她停下来,摁灭烟头,猛地合上相册。
飞蛾已经不动弹了。
只有一张。她往回走,只有一张,不会碍事。
路灯从背後照过来,影子堆叠在脚尖,她每迈一步都踩在阴影中。
-
“你不能说还没想好,应该说在哪,什麽人。”年锦思说。
她们围坐在油腻的木圆桌边上,彼此构成一个看似稳定实际上摇摇晃晃的不等边三角形。小孩蔫头耷脑,抠自己的手指头,庄晓蝶不停喝水,因为年锦思又在问她不想回答的问题,并且非常想抽烟,年锦思两手放在膝盖上,神情严肃,还在等待答复。
庄晓蝶一言不发,边往外走边掏打火机。昨晚在休息站买烟时附赠的一次性打火机,红色,塑料壳子看起来油乎乎的,实际摸上去干涩,小时候这种东西上总印各种姿态的美女,如今最多两行字广告,或者什麽都没有。她走到马路边吸烟,眯着眼看车轮滚滚,卷起浮尘。年锦思没有跟出来质问,因为带了个孩子。年锦思冷着脸,此时却意外的负责。
她们开了一早上,临近中午,经过路边村庄,看到有家小饭馆立在路边的牌子,遂停下来,吃个饭再走。小孩蔫蔫的,看起来没什麽精神。但是很乖,跟在後面不哭不闹,坐下来後抱着水杯喝水,安静得不像个孩子。庄晓蝶回头看小孩,仍坐在原地,她在思考相册里那张照片。
或许终有一天,这孩子会知道是自己和年锦思杀死了他父亲。到那个时候,他会怎麽想?这样揣度未免冠冕堂皇到可笑。
摇醒孩子前,年锦思问她,孩子找个什麽样的人家来养?庄晓蝶回答得很诚实:还没想好。
年锦思不满意这个答案。庄晓蝶知道对方在想什麽,她们不是去郊游,而是要处理一具不知道腐化到什麽程度的尸体。也不知道这具尸体是否已经被人发现,更不知道真正到达目的地後,将要面对怎样的状况。
这小孩绝对不能带在身边。可又能把他交给谁?
老板开始上菜,老土鸡炖汤和两个炒菜,两下上满,庄晓蝶往回走,眼睁睁见老板弯腰看了看小孩,又擡头对年锦思说什麽。她心微微提起来,接着年锦思擡手背贴住小孩额头,又摸了摸自己的。然後年锦思的脸转过来,向她招手。
“发烧了。”年锦思说,“你摸,这麽烫。”
“哪有药店?”庄晓蝶问老板。
“往前两百米有个诊所。”老板说。庄晓蝶和年锦思对视一眼,她们不想增加见过自己脸的人,实际上,如果不是车上有个小孩,中午这顿饭都不一定要正经吃。
庄晓蝶问老板有没有体温计和退烧药,她们照价付钱。老板是个四十左右的女人,爽快又热心肠,主动让小孩躺後屋里的小床上,说自己家里有孩子,儿童退烧药应该还有剩,给她们找了来。
孩子吃了几块鸡肉,喝了小半碗汤,乖乖服了药就躺下了。庄晓蝶坐在床边,年锦思和老板说完话,回到房间里来,看起来有点焦虑。庄晓蝶知道她在算时间。
“那个问题的答案呢?”年锦思问。
“你知道前几天住的小区边上那个广场吗?”庄晓蝶说,“那里有个小孩,十岁开始就自己在那游荡,靠捡空水瓶卖钱丶帮打下手过活。白天做事,晚上打地铺睡大街。现在估计十三四岁,营养不良,一身的病。前阵子才被送回家。”
年锦思不语,眉头不耐烦地拧着。
“我只是不希望这个孩子变成他那样。”庄晓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