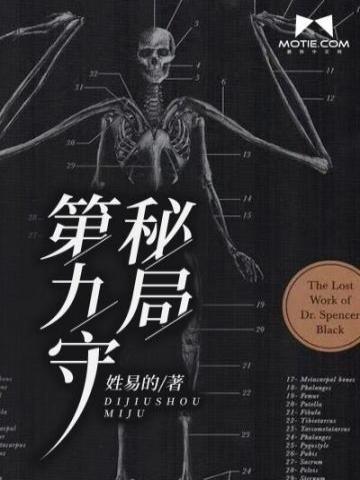紫夜小说>几处早莺争暖树的意思 > 10 旱情(第1页)
10 旱情(第1页)
10旱情
“竹月,你看我阿爹,可从圣上那里吃过亏?”
她冷静下来:“这倒没有。”
“那给东方皇家烧香吧,一晚可不短,阿爹就是拆金銮殿,时间都够了。”
倒不是对皇家太过蔑视,是皇帝实在派错了人。哪怕是叫赵大人来请,阿爹都能好说话些。但偏偏是让最大的对头钟离丞相来,那阿爹既然真去了,差不多也就是奔着撒气去的。
将军府的书房在竹林深处,竹月留在外面,尉迟媱一人踏幽径而入,推开花窗木门,便看到了尉迟夫人。
夫人正斜坐窗前,月下看书,钗环皆是玉质,通体素雅端庄。
闻声擡头看见女儿,眉目间便宛如被月光层层漫过,温婉慈爱地招手:“阿媱来,不怕,你睡一觉,明早阿爹就回来了。”
她朝尉迟媱展开双臂,素色长袖,一展如月华。
尉迟媱本来也不怕,但走过来让阿娘抱一抱,是为让阿娘放心。
尉迟夫人笼她发间,忽然笑起来:“你今日是和未白一道玩去了?难怪府上找不到你,也找不到白术。”
她诧异:“阿娘现在是如何得知的?”
夫人的脖颈微朝後,皱起美人眼,做出戏玩的夸张表情,点着女儿的鼻尖,笑语嫣然道:“我的阿媱好笨,我的阿媱不知道,身上可都是薄荷香呢。”
她忽地记起相府马车中,确实泡着清爽的薄荷叶。
“阿娘喜欢这薄荷香?”她叮铃说着,也去摸尉迟夫人的长发,柔顺轻软,乌黑如墨,“阿娘要喜欢,我去问钟离要些,能让阿娘天天闻见。”
“天天?”她笑着,眼睛看向窗外,再回首时,容色依旧是洗尽铅华的美丽,只是笑意淡些,“阿媱还小,不明白,好物就要难得,如若次次得偿所愿,哪怕是清绝无双的薄荷香,恐怕也会沦为心中凡品。”
她追问:“可如若心想,却还需避忌,阿娘就不感到难过吗?”
“你定也要避忌,这铁一般的将军府,终年挥刀指向他人,眼看是那被刀指着的人,颤颤想着避忌,可我们握刀之人,才是离刀最近的,我们怎能不避忌?”
这番话,尉迟夫人极温柔地讲,扶正女儿头上金钗,她声音一如丝竹乐声的柔婉:“你阿爹再威武,不打仗的时候,也是在这京都皇城受闷气,他岂非是不愿在边境的巍峨山岭,以男儿之性,以将军之威,自在地纵马飞驰?可是家在这皇城京都,阿娘在这里,阿媱也在这里,你阿爹护着我们,便终是走不开的。”
再温柔的语气,都掩不住深处的遗憾。
尉迟媱昂首果断地说:“北境也有阿翁的将军府,在这京都待腻,我们便搬去北境,那才好!”
尉迟夫人抱她更紧,摘下头上的一副玉篦,巧意插在女儿鬓边,说:“你舍得下这京都的繁华,果真是尉迟家最好的女儿。可不在京都的将军府,于这京都,便不是将军府。高处的人,要这下面的高处,也向他跪倒臣服,可如若穿着将军盔甲的人,是个要跪便跪的,没有脊骨的人,在外,又如何有那气吞山河的威慑,来使北境的百万之兵,半步都不敢越界?”
将尉迟媱抱在怀中,她的长袖掩着女儿的头发,目光厚重地,再次看向了窗外高悬的明月。
“阿娘是感觉出来朝中有事?在担忧?”
她轻声慢语:“朝中从来都有事,只是有时,还吹不进将军府罢了。”
“那这回,是钟离丞相把风吹进来了?”
尉迟夫人这时回头,簪紧那玉篦:“无碍,我的好阿媱,风吹进来也只当是玩吧,千军万马都未让将军府倒下,这些风,又算什麽呢。”
尉迟夫人在月下拍着她的後背,衣香舒雅,她恍然记起今日潭边,也曾这样拍抚过钟离未白。
只是带着体温的怀抱,温暖也是暂时的。
翌日晨曦,宫中消息以最快速度传遍京都。
定远大将军自请前往东部三郡,赈济旱灾。圣上应允,并欣然感念,将大将军留在宫中过夜,他们君臣知己,彻夜把酒言欢,一直十分亲厚。
且不说这假模假式的话为何会流于宫外,但任谁听了,除了沉默,便也只有沉默。
宫城方向,昨夜是御林军出动,足足闹到了天亮。连今早皇城望哨的士兵,都一个个眼下青黑,神情恍惚,仿佛刚刚过去的一夜受够了惊吓,全都失魂落魄了。
尉迟媱才刚醒来,还坐在床上穿衣,竹月就把消息报来。
说到底,不过是阿爹需离京几年,前往东部折腾。
相较于为了战报而出远门,这次奉旨治理东部旱灾,至少免于对外出兵的杀伐,对将军府来说,其实算“平和”。
尉迟媱甚至觉得,阿爹平日在京都的朝上闹腾,也未必不是想早日离了京都,去外面自在。
现下去东部三郡治旱灾丶救百姓,还很符合阿爹看不惯窝囊废办事的上佳性格。
但竹月汇报完,却蹲在床下抽抽搭搭起来,说那旱灾的地方,是如何没有吃食,没有水喝,甚至已经愁到大将军连磨个刀,都没水浇石头。
“无事,阿爹既苦着,又苦不到我们这边,我们便替他多吃些,多喝些,这样写信告诉他,他看着心里宽慰。”
竹月重重点头:“没错,小姐,我们这边定得日日吃好的喝好的,才对得起大将军在外的吃糠咽菜。”
尉迟媱深以为然。
临近午时,尉迟佑才回来,那笑已经咧到耳朵根。步入府中时,他见了竹月就催:“赶紧给阿媱收拾东西,东部三郡,异兽奇多,我带她去玩几年,你且也跟着。”
竹月当场傻住。
那时尉迟媱正在锦鲤池边,兴起挥剑,脸上映着闪闪虹光,比池中锦鲤颜色更胜。
她在扑棱水声里听见这话,收剑回鞘:“那阿娘也一起?”
尉迟佑抚着络腮短髯,嘿嘿笑两声:“自是不能,就因你阿娘留在京都,我才可以走,但要是你也留着,那真是白浪费时间,这京都全是些粉头白面的戏耍玩意儿,还不如随我去东部真正历练。”
他一想夫人,也只管得意地笑:“你阿娘在竹阁里看书,是一年到头都不出府的人,她一个人的头脑顶你这丫头十个,还用得着你担心?而且这将军府外,能为难她的,早被我宰光了。”
尉迟媱无话可说,知道他周密,但没想到是宰得周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