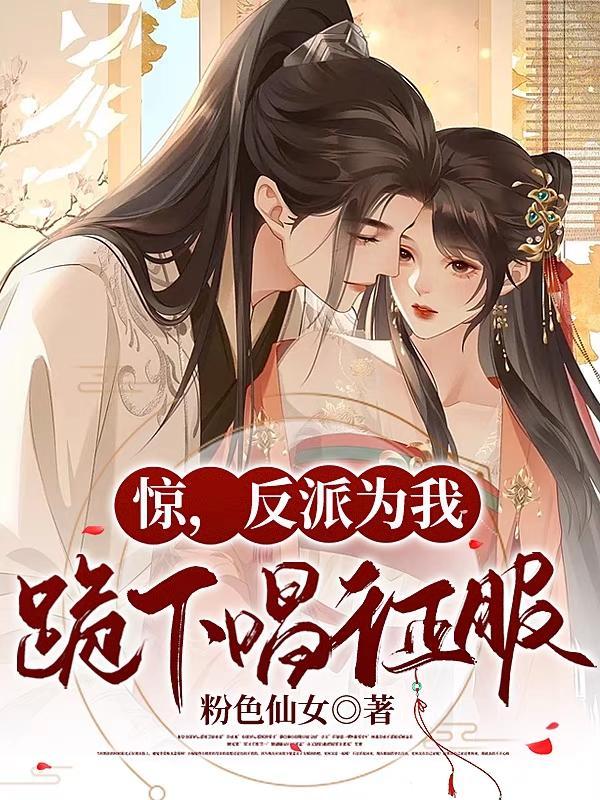紫夜小说>来不及说的那句话作文 > 无声的协奏(第1页)
无声的协奏(第1页)
无声的协奏
风沙在黎明时分渐渐平息。当灰白的光线透过被沙尘糊住的窗户缝隙艰难地渗进办公室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劫後馀生般的狼藉。每张桌子丶每把算盘丶每摞稿纸都覆盖着一层均匀的细沙,踩在地上能留下清晰的脚印。空气里弥漫着尘土的味道,吸进鼻腔带着颗粒感的干涩。
理论组的人们早早来到办公室,面对这片景象,都沉默着。没有人抱怨,大家都清楚时间的紧迫性。陈教授组织大家首先进行清理,用湿抹布小心地擦拭桌面和仪器,将稿纸上的沙尘轻轻抖落,修复被风损坏的门窗。算盘被拆开,珠子一颗颗清理干净,那台珍贵的机械计算器由技术员做了更彻底的检查和维护。
秋雨在清理自己桌面时,首先注意到的就是那支属于凌寒的铅笔。它滚落到了桌脚,蒙上了一层灰黄。她将它捡起,仔细地擦拭干净,看着那依旧尖细的笔尖,昨夜风沙中那个沉稳的身影再次浮现在脑海。她将铅笔郑重地放回上衣口袋,决定今天无论如何要找到机会归还。
清理工作持续了整个上午。午後,计算工作才得以重新开始。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经过风沙的侵袭,加上连日高强度的使用,办公室里的算盘损坏了好几把,剩下的也大多运转不灵。而那台机械计算器,虽然核心部件没问题,但一个负责进位的关键齿轮出现了轻微变形,计算时偶尔会卡顿,严重影响效率和准确性。技术员表示,修复需要专门的工具和配件,至少需要几天时间,还要向总部申请。
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理论组成员的心头。计算是他们的武器,现在武器出了问题,而攻坚的时限却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陈教授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焦灼而无力的气氛。
秋雨看着面前写到一半丶因计算器卡顿而无法继续下去的算式,内心同样焦急。她尝试着完全依靠笔算来推进,但涉及的叠代计算量实在太大,进展缓慢得令人绝望。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王干事带着两个人走了进来,是凌寒和另一位工程组的老师傅。
“陈教授,”王干事开口道,“听说你们这边的计算工具出了问题?工程组那边有一些备用的算盘,另外,凌寒同志说他们工棚里有一台闲置的丶老式的手摇计算器,虽然型号旧点,但维护得还不错,或许可以应应急。”
这简直是雪中送炭!陈教授立刻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了多日未见的笑容:“太好了!太感谢了!王干事,凌寒同志,这可真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凌寒依旧是那副平静的样子,他和那位老师傅将几把看起来半新丶但擦拭得很干净的算盘放在桌上,然後描述了一下那台手摇计算机的情况和用法。
“机器有点重,需要两个人擡过来。”凌寒补充道。
“我跟你去。”秋雨几乎是下意识地站起身说道。话一出口,她才觉得有些突兀,办公室里其他人的目光也落在了她身上,带着些许讶异。
凌寒看了她一眼,眼神似乎微微动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好。”
去工程组工棚的路不算近,需要穿过大半个基地。午後的阳光毫无遮挡地倾泻在戈壁滩上,反射着刺眼的白光。夜里的寒意早已褪去,地面开始蒸腾起隐隐的热浪。两人一前一後地走着,中间隔着几步的距离,沉默像无形的幕布笼罩在他们之间。
秋雨的手指在口袋里无意识地摩挲着那支铅笔,寻找着开口的时机。她能听到前方凌寒沉稳的脚步声,看到他工装後背被汗水洇湿的一小片深蓝色。
“凌寒同志。”她终于鼓起勇气,快走两步,与他并行。
凌寒放缓脚步,侧过头看她,用眼神询问。
秋雨从口袋里拿出那支铅笔,递到他面前:“这个,还给你。谢谢你那天在火车上借给我。”
凌寒的目光落在铅笔上,似乎愣了一下,随即伸手接过。他的指尖再次不经意地擦过她的掌心,带着阳光的温度和一丝粗糙的触感。
“不客气。”他低声说,将铅笔随意地塞进了自己的工装口袋,仿佛那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顿了顿,像是为了打破沉默,又补充了一句,“你的计算,进展还顺利吗?”
他居然会关心这个?秋雨有些意外。她据实以告:“遇到了瓶颈。风沙之後,计算工具又出了问题,现在很困难。”
凌寒点了点头,目光望向远处基地边缘起伏的沙丘,若有所思:“工程组那边,也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理论是完美的,但落实到具体的部件丶材料丶工艺,总是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偏差。有时候,一个螺丝的强度,一道焊缝的均匀度,都会让整个系统失灵。”
他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但秋雨却从中听出了一丝深切的体会。她忽然意识到,他们虽然一个在理论的世界里构建模型,一个在现实的世界里解决具体问题,但面对的本质,或许都是与“不确定性”和“误差”的斗争。
“是啊,”她轻声附和,“理想和现实之间,似乎总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鸿沟是可以被测量的,也是可以被跨越的。”凌寒转过头,看向她,那双深邃的眼里似乎有极淡的光芒闪过,“需要的只是更精确的尺度和更有效的方法。”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骤然劈开了秋雨脑海中某些纠缠的思绪。更精确的尺度,更有效的方法……她一直在思考如何提高计算的精度,却似乎被现有的工具限制住了思维。有没有可能,从数学方法本身入手,寻找一种对计算工具误差不那麽敏感丶或者能够自动修正部分误差的算法呢?
她陷入了沉思,连脚步都不自觉地慢了下来。
凌寒也没有催促,只是配合着她的速度,沉默地走在旁边。戈壁的风吹动着他的发梢和她的围巾,两人的影子在身後拉长,时而交错,时而分开。
直到走到工程组的工棚区,震耳的机器轰鸣声才将秋雨从思考中拉回现实。工棚是用简易材料搭建的,远比理论组的土坯房要粗糙和杂乱,里面堆满了各种金属材料丶零件丶工具,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机油和金属切割的味道。几个满身油污的工人正在一台机床前忙碌着。
凌寒带着她走到工棚角落,那里用帆布盖着一个大家夥。他掀开帆布,露出一台保养得极好的丶看起来有些年头的黄铜色手摇计算器。虽然型号老旧,但每一个齿轮丶每一根杠杆都擦拭得锃亮,显示出主人对它的爱护。
“就是这台。”凌寒拍了拍冰冷的金属外壳,“精度可能不如你们那台新的,但胜在稳定,不容易出故障。摇起来需要些力气。”
他和秋雨一起,费力地将这台沉重的机器擡上一个简易推车。在推动推车返回理论组的路上,秋雨依旧在思考着刚才的灵感。她忍不住将自己的初步想法说了出来,关于如何改进算法以减少对计算工具精度的依赖,语速因为兴奋而略微加快。
凌寒推着车,安静地听着,偶尔在她停顿的时候,提出一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直指她思路中尚未考虑周全的细节。他的问题往往从一个具体的工程实践角度出发,恰恰弥补了秋雨纯理论思考可能存在的盲点。
“……所以,如果能在叠代过程中引入一个自我修正的反馈机制,或许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系统误差的累积。”秋雨总结道,眼睛因为思维的活跃而显得格外明亮。
“理论上可行。”凌寒点了点头,目光落在前方坎坷的路面上,小心地避开一个土坑,“但反馈系数的设定需要非常谨慎,过犹不及。这就像我们调整一个机械系统的阻尼,太小了无法抑制震荡,太大了又会导致响应迟缓。”
这个比喻如此贴切,让秋雨瞬间理解了其中的关键。她惊讶于凌寒能将抽象的数学概念与具体的物理现象如此流畅地联系起来。他绝不仅仅是一个熟练的工程师。
“你……对数学也很了解?”她忍不住问道。
凌寒推车的动作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随即恢复自然,语气平淡:“以前学过一些,工作需要。”
他的回答依旧简短,带着明显的回避。秋雨识趣地没有再问下去。每个人在这里都有不愿提及的过去,这是心照不宣的规则。
他们将计算器运回理论组,引起了小小的欢呼。凌寒简单演示了操作方法,尤其强调了摇动手柄时需要保持的均匀速度和力度。他的讲解清晰明了,没有一句废话。
在他准备离开时,秋雨再次郑重地道谢:“凌寒同志,谢谢你,不只是为了这台机器。”
凌寒看着她,沉默了片刻,才低声说:“都是为了工作。”
说完,他转身离开了办公室,背影依旧挺拔而孤独。
有了这台老式计算器的辅助,加上秋雨受到啓发後开始着手优化的新算法思路,理论组的计算工作虽然依旧艰难,但总算得以继续推进。办公室里再次响起了算盘声和手摇计算器规律的咔嗒声,交织成一曲独特的丶属于这个年代的奋斗乐章。
秋雨在摇动计算器手柄的间隙,偶尔会擡起头,望向窗外工程组的方向。机器的轰鸣声隐隐传来。她想起凌寒推车时沉稳的手臂,想起他谈论阻尼时专注的眼神,想起他那句“都是为了工作”背後可能隐藏的深意。
那支铅笔已经归还,似乎了结了一桩心事。但某种无形的东西,却仿佛在风沙过後,在这一次短暂的同行和交谈中,悄然建立起来。那是一种基于专业能力的相互认可,一种在共同困境中萌生的丶极其微弱的理解和默契。
它无声无息,却像戈壁滩地下深处潜藏的暗流,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悄然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