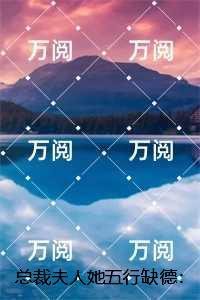紫夜小说>汉川往事上映时间 > 名为分数的墙(第2页)
名为分数的墙(第2页)
————
我妈起初还秉持着“快乐教育”的理念,宽慰我“尽力就好”。
但接连几次家长会後,面对老师委婉的提醒和其他家长谈论补习班时投来的目光,她的眉头越锁越紧。
我见过她深夜对着我的试卷叹气,也听过她和我爸压低声音争论“是不是该管管了”。
後来她似乎下了某种决心。
我被她拉着,走进了数学老师家。
她手里拎着包装精美的果篮和保健品,说着“孩子让您费心了”之类的话。
老师推了推眼镜,笑容和蔼了许多。
“林念这孩子挺聪明的,就是不够踏实。”
从老师家出来,妈妈拉着我,“念念,咱们不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下次进步十分,好不好?”
妈妈的手指有些凉,那种凉从她牵着我的手一直蔓延到心里。
说不清是什麽滋味,像是背负了更沉重的东西。
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课堂上,老师提问我的次数果然多了起来。
那种被额外“关照”的目光,像聚光灯打在身上,让我不敢松懈。
课本丶试卷丶参考书……
它们堆满了我的书桌,也侵占了我望向窗外香樟树的时间。
露露和江远舟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种“培训班”丶“奥数班”的名单上。
我也未能幸免,被妈妈塞进了一个个周末的补习班。
我在夹缝里,像个陀螺,被鞭子抽打着旋转,不知方向。
这种疲于奔命的状态持续了将近一个学期。
直到我趴在堆满练习册的书桌上,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砸在摊开的数学题上,墨迹晕开一团模糊的灰影。
妈妈来叫我休息时,看到我脸上未干的泪痕和面前一片空白的草稿纸。
她看了很久,叹了口气,吹散了某些一直紧绷着的东西。
她摸了摸我的头,“算了,念念,咱们不去了。”
她像是终于接受了一个事实。
她的女儿,或许终究只是芸芸衆生中,平凡的一个。
她主动将我从那个弥漫着粉笔灰和焦虑气息的“囚牢”里,解救了出来。
她看着我说:“咱们就按自己的步子走,能走到哪儿是哪儿。”
当我终于不再执拗于用别人的速度来衡量自己时,我反而能跌跌撞撞地跟上队伍的节奏了。
成绩单上的数字依然起起伏伏,但大多数时候,它终于能稳定在中游,偶尔超常发挥,还能侥幸挤进前十。
对这个成绩,我已经感到满意。
最重要的,我学会了欣赏他们的光芒,也安然接受了自己的温润。
我接受了自己数学天赋有限,但这并不妨碍我依然可以从文字中获得慰藉,在友情中感受温暖。
那堵曾经让我倍感压力的分数墙,不知不觉也矮了几分。
周末,我们窝在沈姨的画室。
陆星野正对着一幅未完成的画冥思苦想,露露和江远舟讨论培训班上的物理题,眉飞色舞。
我靠在窗边,翻着新买的《少年文艺》,阳光暖融融地照在书页上。
江远舟顺手把他觉得好吃的怪味花生分给我一半。
看着他们,心里曾因迷茫而皱缩的角落,被风吹得舒展平整。
那堵墙依然在那里,但它不再能完全定义我们是谁,也无法阻断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