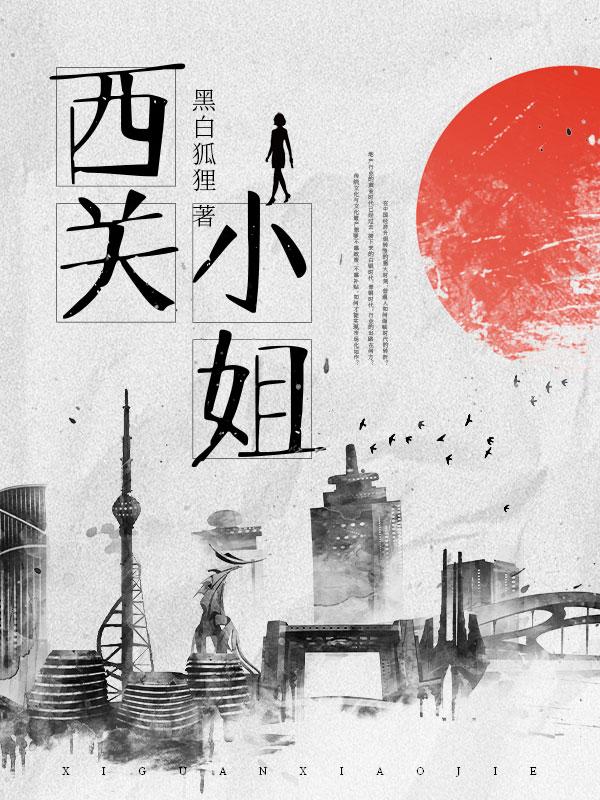紫夜小说>灰色铁轨 > 2(第2页)
2(第2页)
可大学开学後,我左等右等,仍不见李子桐找来,寄过去的信也迟迟没有回应。我多次去她考上的那所名牌大学找她,最後却发现她并没有入学。
秋意萧索的十月,回信终于来了。我感觉身心都凉了大半截,信里她向我郑重致歉,说自己无法兑现原本的约定了。李学强夫妇留下的存款已经快见底了,无法负担她和弟弟同时上学的费用,就算拿到奖学金也不够。同时姐弟两人在城关市举目无亲,若是李子桐来上海,弟弟就得被送进儿童福利院这类的机构了。思前想後,她决定放弃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在老家的一所医院找了份护理的工作。她想先赚几年钱,等以後有机会再复读考学。
我当即打了长途电话过去,想要劝说她回心转意。虽然钱这东西我家也缺得很,实在不知道如何帮她解决问题,可心里就是横竖接受不了这样残酷的未来。电话是她弟弟接的,说姐姐不愿意接我的电话,她想要自己一个人冷静冷静。
後来,来往的信件也断了。
那年冬天,上海没有下雪,我却觉得每天都冻彻骨髓。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经历如此漫长的冬天。等到寒假,我好不容易安顿好母亲,买了回城关市的车票。
从火车站出来,我没回家,先去了李子桐家。在楼道口踟蹰半天,我鼓起勇气敲了门,门只开了一条细缝。
“你谁啊?”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愣住了,半晌才反应过来,“你是李子桐的弟弟李天赐吧?”
“是啊,你到底是谁,有什麽事啊?”对方的声音明显不耐烦起来。
那时的座机电话音质不佳,话筒里的声音和现实中的人声比起来总有轻微的变调。门後男孩的声音明显比之前听过的粗野坚硬一些。
我报上自己的名字并说明来意。
“姐姐不在家。”
“那我能进去坐坐,等她回来吗?”
谁知他根本不愿开门。想想也是,当年的凶杀案应该至今仍留有阴影。
“那我就在门口等好了,她大概几点回来?”
门对面传来一声嗤笑,“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姐姐她根本不想见你。”
我不由得心头火起,“你知道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吗?”
“当然知道了,你不就是那只一直缠着她不放的癞蛤蟆吗?姐姐常常背後说起你做的那些蠢事,拿来逗乐子。”他的声音带着阴湿的笑意。
像有一大盆雪水从後衣领灌入。
“实话跟你说吧,她今天和男朋友出去玩了。鬼知道今晚会回家还是在外过夜,你愿意等,就在门口慢慢等好了。”
像一只游魂似的,我在熟悉而又完全陌生的城市没有目标地晃荡。
街灯亮起,夜空中飘着细雪。不久後越下越大,风雪交加,路上已不见其他行人的踪影。但我无法停下脚步,也不知道该去哪。只知道一旦驻足不前,体内支撑我好好活到现在的体系就会因为自重崩溃,精神将会失去支点,坍塌成一个什麽也不是的存在。
柏油马路到了尽头。我沿着一条勉强成型的土路继续走了下去,穿越过荒野和小树林,一个无法穿越的水体突然横在眼前。
是水库。我曾和李子桐在这里拍过电影。回忆起来就像前世残留的记忆一般古老。
我久久伫立不动,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落下,在肩上积累起来。不如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变成雪人,和时间一起冻结在岸边算了。月亮藏身在棉状的云絮後面,视野像泼墨画一般的昏黑。只有湖面收集来微乎其微的光线,勉强显示出水面涟漪的存在。
那个不眠的冬夜,月亮始终没有出现。
我没和父亲见面,直接逃回了上海。
四年大学生活没什麽可说的。感谢有衆多选修课可以上,我把大部分时间都投注在学习上,即使没有学分也不介意。毕竟无论是解微积分习题还是记忆历史年表,都没有感情介入的馀地,与做其他事相比轻松得多。
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帮助下,母亲找了份社区的编外工作。工资微薄但压力不大,她的精神状态得以稳定下来,但仍不时需要人照料。我不得已放弃了住校生活,留在压抑的老公房里继续过日子。
除了有课的时候我都不会去学校,因此很难融入班级群体之中。与高中时代的最後一年一样,大部分时间我都自己一个人打发,看看电影,看看书。不用照顾母亲的日子,就去出门透透气,在人民公园的长椅上读书消磨掉一整天。
不过,若真要总结大学时代交不到朋友的原因,恐怕不是一句“没有住宿舍”可以解释的。归根结底,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我对与人的来往失去了兴趣,大学同学们看起来都充满青春活力,但实际聊上几句,就会发现话题枯燥且单调。引起我的兴趣,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说更多的话的对象一次都没遇到过。
由于总是一个人闷头读书,毕业季过了大半,我才後知後觉地发觉早该找工作了。身边的同学纷纷确定了去向。至今未做任何准备,错过了大把校招会的白痴好像仅我一人。
我急忙补写简历,四处投递。但不知道是因为我大学四年没有做任何可吹嘘的实事以至于简历过于单薄,还是各家企业的招聘指标已经满额了,投出的简历全部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刚巧那段时间外祖母因病去世了。她留下遗嘱,把老公房留给了隔一两年才会回家探望一次的小儿子。照顾病榻上的外祖母度过最後几年,换汤换药,清洗尿壶的母亲则一分钱也没分到。她为此和我的舅舅大吵了一架,对方勒令我们在一个月内从老公房里搬出去。
母亲的收入显然不足以覆盖我们两人在上海的生活开销。我小心翼翼地提出建议——要不搬回城关市生活算了。
“早回不去了。”母亲手里紧紧篡住她的药瓶,“那里已经没有家了。”
时间紧迫,我取出大学时代打工攒的所有存款,租了间只有30平方米的单身公寓。虽说甲醛气味浓重,但好歹把自己和母亲都安顿了进去。同时找了份超市收银的工作,先领上工资再说。
由于夜班工资高,我主动申请调了岗,每天干到凌晨两三点才回家。一个人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无人的街上,我不得不给自己打气,要在这个城市活下去,必须摒弃软弱的个性,变得更加坚强。这份决心至今也未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凝固下沉,变成了我人生的基石。
公司的办公室位于53层,从落地窗望向窗外,浦东的夜晚已迎来终结,江面上闪烁着曙光的碎片,街上开始有车驶过。
我深吸了一口气,放下咖啡杯,关上音乐,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当中。
![(历史同人)[汉]穿成武帝家的崽+番外](/img/23399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