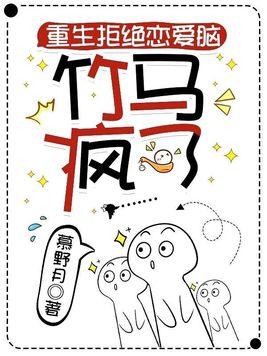紫夜小说>从萤火虫到人工冷光阅读答案 > 第121章 夜会 晋王妃你喜欢这样吗(第2页)
第121章 夜会 晋王妃你喜欢这样吗(第2页)
从萤缩在散了热气的衾被中,翻来覆去地不住叹息。一会儿发愁朝廷对谢玄览的态度,一会儿又惆怅二人之间的关系,又冷又愁,彻底没了睡意。
正想起身去重写书信时,忽然又听见外窗响动。
竟然是谢玄览去而复返。
他被外面刺骨的冷风一吹,心凉了,头脑也冷静下来。无数伤心都变成想要报复的恨意,驱使着他又原路折返。
“我觉得你方才所言极有道理。”
从萤拥衾望着他,不解道:“什麽?”
谢玄览笑了笑,说:“我若问的话太多,今夜就成不了好事,倘若不能两情相悦,如此糊里糊涂得一夜安寝也不错,长夜漫漫,足慰寂寥。”
从萤心说,她并不是这个意思。
谢玄览擡手卸了腰带,一边解衣扣一边低眼瞧她,那是一种极放肆丶极具侵略性的目光,似乎在盘算从哪里开始将她拆吃入腹。
他带着凉意的手掌握住她的脚踝时,从萤浑身打了个冷颤,她本已经够冷了,他还将霜夜的凉意带进来,冰得她情不自禁要往里侧蜷缩。
却被牢牢锁住,双膝与手腕皆不得动弹,像在衾中戴了枷。
细密的吻沿着鬓角落在她耳边,他呵出的气息是炙热的,冷热相激,更是一阵颤颤的痒。
他在她耳边含笑道:“咱俩先来串个供,今夜算我有失君子风度,强迫与你,将来他若问起,也免得你难做,怎麽样,晋王妃,如此你可喜欢?”
从萤擡头堵住了他的嘴。
冷意很快就驱散了,到後面开始热得出汗,青帐之内氤氲生春。
年轻的身体,有发泄不尽的欲望和爱恨,从萤只剩喘息的力气,一只手腕探出青帐,又被拖回了狂风暴雨里。
“热……”她焦渴的嗓音听起来有几分可怜。
身上一轻,终于得了一点呼吸,过了一会儿,一杯在炉上温过的水递到她嘴边。
青帐开合的间隙,透进一片月光,从萤看清了他身上新旧交织的伤痕,最新的一道在肩头,被薄汗洗得红艳如一绽桃花。
她心疼极了,指端从旁边抚过,问他当时如何受的伤。
谢玄览却不为所动,捉住她的手往下走,说道:“有这些虚情假意的力气,不如多许我一些好处。”
这一夜翻来覆去,大有要折腾到同归于尽的意味。
直到隐约听见鸡鸣,从萤昏昏沉沉的意识才有了几分警觉,推了他一把:“快走。”
谢玄览在她耳畔轻笑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你该留我才对。”
从萤说:“你不是君子。”
“那谁是,晋王吗?”
从萤沉沉叹了口气,心道,他怎麽又提这壶。
幸好谢玄览也不算全然昏聩,没打算留到侍女们进门,又讨了一回好之後便起身穿衣,神清气爽将埋在被子里的从萤捞出来。
对她说:“我今夜还来找你,咱们在西州多熟悉几回,将来我去晋王府找你时也能驾轻就熟,是不是?”
此人怒到极致,反而成了刀枪不入的金石,再不似之前那般一戳就炸,也变得更加不好应付了。
从萤费劲浑身力气抽出一个荞麦枕头来砸他:“快滚。”
心想,还是晋王待她好,既然都是三郎,怎麽晋王就比他体贴呢?
*
事实上,除了从萤,没人觉得晋王与“体贴”二字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