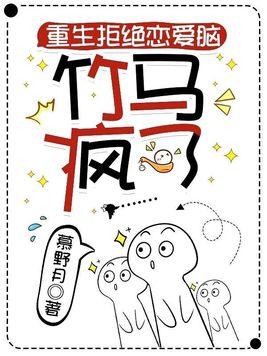紫夜小说>从萤火虫身上得到的启示 > 第92章 偷跑 阿萤到我这儿来(第2页)
第92章 偷跑 阿萤到我这儿来(第2页)
谢玄览端详着晋王:“殿下到底是何方神圣,是因死过一回开了天眼,能预知未来事,还是方外神仙托身成人,要来化危解难?”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根本是个故弄玄虚的骗子。
对于从不信神佛的谢玄览而言,这二者已是他能想象的极限。
晋王取出一个木匣推到谢玄览面前,打开,里面装着半面古旧铜镜,背书“照”“宝”二字,正是太霄道人曾赠与的宝物。
晋王说:“物归原主,能知晓多少全看你的造化,其实不知道更好,于你于我,都少去许多烦恼。”
*
从萤生病了。
她在流杯亭中直站到入夜,後来下起雨,风露侵透了她的肌骨,一直冷到心底里,她就病了。
晋王派人看守集素苑,请来张医正,送了药材,通通被从萤拒之门外。她出不去,身边只有紫苏,昏昏沉沉时隐约听见过喧嚷,醒後问紫苏,紫苏说:“是谢夫人来过。”
谢夫人想带她走,奈何拗不过晋王。
从萤卧在枕上叹息道:“三郎离开後,谢氏如断一臂,只怕以後……”
话未说完,她又偏头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在一阵清苦的药香中苏醒。
眼前是新婚夜的鸳鸯枕,早秋凉风拂开喜帐,望见案头龙凤喜烛尚在,瓶中插着鲜艳棠果,围屏上仍贴着她和谢玄览一同剪出的双喜字剪纸。
屏面上,朦胧映出一个颀长玉立的身影。
从萤怔然出声:“三郎……”
那人闻声转来,却是晋王,从萤目中期许的光彩沉潜黯然,不知该说什麽,闭上眼睛转向床内侧。
他走近了,药气也渐浓郁,耳边听见汤匙搅动碰撞的声音。
泠泠的,同他的声音一样温和:“我知你不想见我,可你生病却捱着不肯喝药,那就不得不见我。来,把药喝了再睡,否则紫苏徒劳辛苦这两个时辰。”
他太懂得如何拿捏她,从萤心里不是滋味,蹙眉将眼睛闭得更紧。
听见晋王说:“你昏睡这两天,谢三已到宣州,送了信给你。”
从萤心中微动,睁开眼,见晋王右手端着瓷碗,左手捏着信封,眉眼含着淡淡的笑,却先将药碗递到她面前。
“先喝药,这药清苦,我就不动手喂你,免得你更恶心了。”
从萤端过药碗饮尽,目光落在他左手的信上,晋王却得寸进尺:“喝完药,再下来吃点东西。”
从萤披衣下床,简单洗漱,走出碧纱橱,在摆了清粥盐齑的团桌边坐下。饭菜都温得刚刚好,从萤确实也饿了,却不愿叫晋王看出来,所以用筷子搛着粥中的米,一粒一粒吃。
见她如此不情愿,晋王叹息着拆开信:“我读一句,你用一勺,行不行?”
从萤没有反对,便当她是默许了。
“吾妻阿萤亲啓。”
从萤筷子顿了顿,心道,这也能算一句吗?
等不到下文,她只好慢慢拾起勺子,尝了一大口粥。
待她咽下,晋王继续念到:“途次顺遂,今已抵宣州。”
从萤又舀起一勺,晋王给她搛了几片青菜。
“惟念卿玉体康宁,忧心悬悬。”
“……”
“盼与卿拨云相见,顺颂妆安。”
这封信写得文雅缠绵,关切备至,如情人在耳畔喁喁私语。从萤却突然将粥勺扔回碗里,冷声道:“三郎走了两天才到宣州,这信是长了翅膀飞回来的吗?”
伎俩被戳穿,晋王只是笑了笑:“还好,没病糊涂。”
从萤气噎,起身又回去躺着,听见晋王在外面吩咐些什麽,过了一会儿又走进卧房来,停在围屏外面。
从萤怔怔望着他落在屏面上的影子,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个人。
晋王隔着屏风说道:“这两日我暂不过来扰你清净,等你养好病,谢三到了西州,我就不会再拘着你了。”
说罢,屏风上的影子渐渐淡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