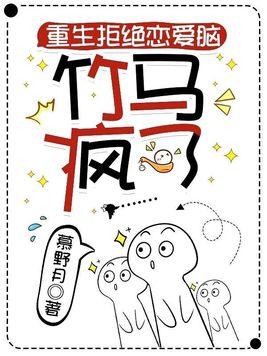紫夜小说>与里斯克小姐的奇妙故事在线观看 > 2 5(第2页)
2 5(第2页)
我呼吸一窒,玛格丽特怨毒的控诉和那冰冷的微笑瞬间冲回脑海。
亨利·沃尔特。
玛格丽特·沃尔特夫人的丈夫。
他害怕他的妻子戳破他的真实想法,讲出不能为外人道的心思,却不知他的妻子在诉说着如何的去报复,去谋杀他。
这对据说曾经完美的夫妻。
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一个出于怨恨一个出于利益。
简沉默了一会,仅仅一会。她的眼神没有丝毫闪躲,反而像平静的湖面,映出亨利阴郁扭曲的倒影。
“沃尔特夫人沉浸在她巨大的悲伤里,先生。”简的声音依旧清晰冷静,却透着冷意。
“她谈论失去的孩子,谈论她曾经相信的……完美幻象。幻象的破灭总是令人心碎,尤其当它曾被视为信仰。”她的话像软刀子,精准地刺向亨利最虚僞的痛处。
亨利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那抹假笑消失了,只剩下冰冷的阴沉。
“悲伤?哈!”他嗤笑一声,声音陡然升高,报躁,“她的悲伤就是制造流言,歇斯底里,毁掉一切!听着,小姐们,”
他向前又逼近一步,距离近得我能闻到他身上残留的,令人作呕的甜腻香水味和淡淡的……金属味?(铅中毒可能的体味?)
“我不管你们在她那个疯人院里听到了什麽。这是我的房子,我的家事。聪明人,就该管好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然後……闭上嘴。把听到的,看到的,都烂在肚子里。明白吗?”
简只是冷漠地看着他。
“弗瑞,记住,我们一开始什麽都不知道。”
当里斯克又在重复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正在下午一点回伦敦的火车车厢里。
所以,发生的一切本就和我们无关。
“这是一对‘完美’的伴侣,至于是佳偶还是怨侣,弗瑞,这是没有必要的问题。”
“任何人,首先都是他们自己,他们该为自己做下的一切,而承担。”
“可是……”我张了张口,却不知道怎麽说下去。
简抱了抱我,什麽也没说。
侦探不是上帝,无权审判或拯救。
而在这样复杂纠葛的事件里,无论我们做什麽,即使是报警都是对另一方的不公平。
上帝在天堂俯视衆生。
祂是否真的注视着,以至于让曾经或许相爱过的两个人成为这样。
我迫切地需要一些东西来转移注意力。
“简,你怎麽知道沃尔特夫人在沃尔特先生的瓷杯里下毒的?”
“下毒?不不不。亲爱的弗瑞,是铅。”简说。
“是沃尔特先生钟爱的鲜艳漂亮的瓷釉。也许这给了夫人灵感。而我们的沃尔特夫人,只是做了点手脚,加剧了它的致命性。”
“少量醋酸铅,日复一日,而我们的沃尔特先生,刚巧需要浓厚的咖啡。玛格丽特足够聪明。”
简看着窗外说。
“但是?你怎麽发现的?”我有些气馁,明明我和简一起,但是我却没有发现这些东西。
“哦…弗瑞,我只是比你多了点运气。看见她在药房的单据。”
“只要说治疗皮肤病或者染发。她肯定已经在不少的药店买过了。而老约翰告诉我,当先生不在的时候,夫人总是偷偷独自出去。”
我想起简问过我的关于时间的问题,甚至又些兴奋了。“哦,简,时间!她一定是先去了药店,再来找的我们!”
简又笑了,浅绿色的眼睛亮亮的,她不说话,拉着我看外面的风景。
“好啦,弗瑞,别想了,看看风景。”她说,“也许我真的应该把买车提上日程,到时候带你去兜风。”
我也被她带偏了。
去思考到底买什麽样的车。
读者们,当我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当时沃尔特先生紧随其後。
他究竟是否知道呢?
或者说,她究竟是否知道呢?
在这件事情没多久。
我和简的事务所(我喜欢这麽叫),查令十字街12号,收到了一张慷慨的支票。
署名,玛格丽特。
後来我们听说,富有的沃尔特夫人依旧住在那座巨大的庄园里。
晨昏交替,只有两个娃娃的影子,陪她走过漫长回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