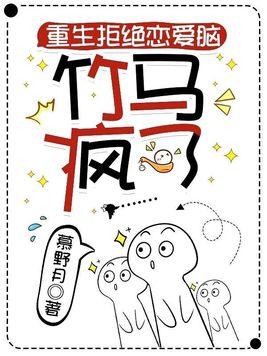紫夜小说>皇上今天催更了吗 > 第12章(第1页)
第12章(第1页)
“最明显的一个好处是,帮了帝后的忙,宫里但凡有用得到僧人道人的事,就会请他们前来;他们不肯,多的是想要那份殊荣的。宫里的钱好赚难赚放一边,可只要有本事长期赚,香客便会趋之若鹜。”
方美人听了,逸出动听之至的笑声,“凡事让娘娘一说,便是那明明带着仙气儿的,也要染足烟火气。”真正的意思是,一番话要是让空明、叶天师听到,情何以堪?
贺兰悠也笑,“有本事就别收香油钱。”
方美人笑够了,深思起谢家的事,轻声道:“嫔妾怎么觉着,娘娘存了除掉谢家的心?”
贺兰悠目露欣赏,“聪明。真庆幸,太后和谢德妃没你这份儿机敏,不然可有的头疼了。”
“嫔妾恨不得与母家恩断义绝是真,另有些用得上的益友也是真,午后便传话出去,请他们观望着谢家动向,伺机而动。”
贺兰悠从善如流,“也好。”碍眼的墙,加力推一把的人越多越好。
至于萧灼那边,贺兰悠一丝顾虑也无。
事情明摆着,萧灼原本的打算,是用谢家制衡贺家,再一步步化解贺家的势力乃至铲除。
贺兰悠承认,横死的谢国公是块料,能凑合着用。可皇帝用他的代价是她父兄及至满门的生死,那还是省省为好。
对谢家、谢国公,贺兰悠当真花费过很多精力人力财力,斟酌出了很多反手回击制衡的策略。
当哥哥的生死成为萧灼一步棋的时候,贺兰悠激愤之下,看到一条捷径:
谢国公或许是用兵的料,但他到底在军中没有威信,不似贺家男儿一般,骤然殒命势必引发一段时间的军心躁动。
既然对大局没有妨碍,杀了不就得了?谢国公死的结果,只能是刑部锦衣卫白忙一阵,铁血男儿会否听说都未可知。
难不成留着谢国公,害得父兄陷入长年累月的水深火热?
——贺兰悠是这么想的,也这么做了。
如今谢家父子一死一残,完全不能指望,谢国公嫡出次子不学无术,家中再怎么想栽培也有心无力。
谢家已经完了。
萧灼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了,不然不会那般恼怒,可再恼怒也得面对现实,料理自己一念之差弄出的烂摊子。
贺家动不了了,趁机让谢家倒台,对皇权也有诸多益处。
太后和谢德妃已经成了秋后的蚂蚱,只不知意识到了没有。
自然,贺兰悠也不会掉以轻心。前人给出的经验而言,秋后的蚂蚱也有结结实实蹦跶一阵的。
两仪殿中,萧灼跟面色奇差的太后摆事实:“日后您切勿接近皇子公主,否则,皇后少不得将此事公之于众。朕的意思是,您好生安抚皇后,要不然,不论是何情形,皇后大抵都不会再帮您隐瞒。”
太后嘴角翕翕,半晌才怒道:“只凭两个人的占卜,就定了哀家的命格?”
萧灼慢悠悠提醒她:“无人不知,太后对空明大师推崇备至。”
太后噎了噎。帝后都不信佛又不信道,宫中各类法事素来循旧例行事,倒是她礼佛数十年,近几年常命人去请空明大师进宫讲经,空明已到了超然的地位,不能随叫随到,她便退而求其次,常碰面的是空明的师弟、徒弟。
思量片刻,太后索性混横不讲理了:“好,就当这是真的,哀家也不怕闹得天下皆知。既然哀家与皇后、皇后所生的儿女八字犯冲,那就请皇上下旨,命皇后携儿女住到行宫。总不能说,皇上不顾孝道,要哀家长年累月躲着谁不见。”
萧灼笑若春风,眸色却愈发深沉,“若如此,朝臣怕是要争论一番,孝道、子嗣何为重。况且,朕近年来也不安生,不如依着您的心思,携妻儿常居行宫。”
太后哽住,慢吞吞踱步一阵,总算冷静下来,落座喝了两口茶,道:“哀家知道,皇上有诸多不得已。也罢,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皇上如能答应哀家两件事,哀家会择期迁居行宫,给你和妻儿一份心安。”
“哪里有那么多非此即彼的事。”萧灼望一眼窗外,“该用午膳了,您要与朕一起么?”
竟然根本不接受谈条件。太后面色青红不定,难堪地起身,“哀家回宫了。”
萧灼起身送了几步。
回到慈安宫,太后压抑着的怒火爆发,摔了一地的茶具摆件。
跟过来的谢德妃瞧着,茫茫然不知所措,待得太后折腾得累了,跌坐在软塌上喘粗气,从宫人手里接过一盏茶,奉给太后,“姑母消消气,还需从长计议。”
太后将茶盏掼在矮几上,瞪了她一眼,迁怒道:“都是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害的哀家!好端端的,怂恿哀家见那两个孽种做什么?”
“是,都是侄女不好,可我初衷是好心啊。”谢德妃眼中泛起泪光,“谢家的前程,如今全系在我们身上,我是想着,法子不论高明与否,都要试一试。”
“试出来的结果是这样,你满意了没有?”太后仍旧没有好声气,“倒是说说,眼下该如何是好?”
谢德妃权衡再三,硬着头皮道:“恐怕只能依皇上所言,安抚皇后一番,好歹别让她大肆宣扬命格的事。不论我们还是谢家,真的禁不住雪上加霜的事了。”
太后沉吟半晌,长长一叹,“皇后时时夜不安枕,等会儿你替哀家选一柄玉如意,差人送到昭阳宫,请皇后晚间过来用膳。”
“是。”谢德妃打起精神,笑着建议,“晚膳您加几道菜,御膳房一定知晓皇后的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