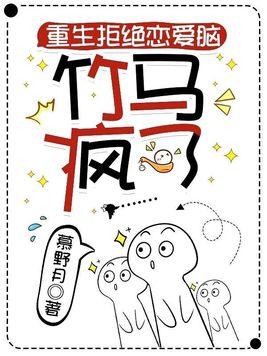紫夜小说>玉腰藏春富贵金花 > 第7章(第1页)
第7章(第1页)
情急之下,宋蝉已顾不上什么礼数,抬手就紧攥住陆湛的袖:“大人不觉得那条蛇与您不亲近吗?若民女没猜错,您用来引蛇的香料来自鄯善。”
门口守卫的半只脚已迈进门内,陆湛挥了挥手,又让他退了出去。
这条灵蛇的确是他月余前从鄯善商人手中购得,如今还不能做到完全听话。
他本以为是与灵蛇磨合时间不够,宋蝉的话却让他起了兴趣。
“说下去。”
宋蝉松了一口气。
“大人可试着在香料里加一味穿心莲,或许能有效果。”
陆湛抬眼,深深扫向宋蝉。
没想到这民女除了皮囊之外,也并非一无是处。
与陆湛面谈之后,宋蝉便关在另一间独立的牢房。
牢房的布置依旧简陋冷清,不过终于不用听沈家贵女们的冷嘲热讽,倒很是清净。
但只过了几天,她便发觉这种望不见头的孤独才是真的难熬。
那次谈话到最后,陆湛什么也没说。
既没有允诺能放她出去,也没有说要将她如何处置。
只是将她单独安置在这个房间,每日固定有人送水送饭,其余没有任何音讯,仿佛那场对话根本不曾发生过。
宋蝉也曾试图与那些送饭的刑吏打探消息,可陆湛手下的人都和陆湛一样冷血无情,从不理会她的搭话,甚至还威胁宋蝉再多嘴就割了她的舌头。
她摸不透这些人,也猜不透陆湛的心思。
或许陆湛也根本不想让别人猜透。
入夜后,宋蝉躺在茅草堆上,透过高窗看天际的一抹星光,忍不住想,这命运实在是造化弄人啊。
整件事最无辜的人,就是她自己。沈家的人至少曾靠着贪墨的钱过了几十年锦衣玉服的日子,而她有过什么?
在花月楼里这十年受尽冷眼欺负,以为要迎来曙光,却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爹”,将她再次拉入深渊。
私狱寒凉,这几日她膝盖旧伤愈发严重,尤其夜寒露重时,就像被千万根针刺,痛得她睡不着觉。
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之际,牢房的门锁忽然响动,宋蝉睁开眼,竟看见一名狱卫站在门外。
“陆大人要见你。”
已是丑时,陆湛屋里仍然烛火未熄。
桌上堆满了千鹰司奏事的册子,侍者在旁为陆湛掌灯研磨。
狱卫将宋蝉带进屋时,陆湛还在低头看着册子。
宋蝉站在门边,想到上次的情形,不敢再上前去,生怕那毒蛇不知又从哪里钻出来。
手中那本册子看完,陆湛提笔批了几字,虽未抬头,却好似已将一切尽览眼底。
“就打算在那站一夜?”
宋蝉不得不走上前。
烛光流转照印在陆湛捻笔的修长手指上,没由来地,宋蝉的感到后颈一阵酥麻,又浮现那夜他掌心粗砺的触感。
“沈家的人,半月后问斩处置。”
宋蝉微微一怔。
燕朝刑律对贪墨一向严格,前朝曾有先例,那官员被生剥了皮,身体填入稻草被放置在闹市街头,以震慑百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