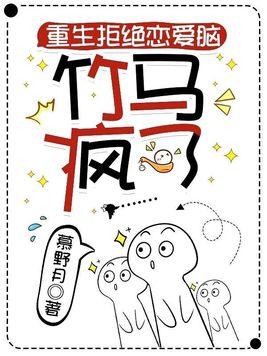紫夜小说>幕后无弹窗全文免费阅读 > 取景器(第1页)
取景器(第1页)
取景器
天还没亮,旧仓库的卷帘门只拉起半人高。
郁燃蹲在门口,把一台老式Arriflex35mm摄影机抱在怀里,
像抱着一台被遗忘的留声机。
镜头盖没开,取景器里漆黑一片,
他却把眼睛贴上去,像在凝视一口深井。
仓库里只有一盏钨丝灯,
灯丝在玻璃罩里微微颤动,像一颗不肯熄灭的心。
他把取景器对准地面水洼,
水洼里映出一点将亮未亮的天光,
像一块被提前曝光的底片。
06:00,他把摄影机搬上改装皮卡。
车厢里铺着防震棉,
旁边放着那只旧黑伞和那枚内侧空白的铂金戒指。
他把取景器对准母亲病房的方向——
医院在城东,
他却在城西的旧仓库,
中间隔着40公里雾霾。
取景器里看不见母亲,
却能看见自己指尖的颤抖,
像一条被拉长的胶片齿孔。
他对着取景器说:
“今天,我把馀生剪进取景器。”
声音低得只有取景器能听见。
08:00,他把摄影机对准手机。
屏幕停在“江聿丞”三个字,
听筒里依然是冰冷的机械女声: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取景器里,手机屏幕的蓝光被放大成一片冷白,
像一片被剪坏的胶片。
他把手机关机,
像把一句没说出口的再见折进取景器。
他对着取景器说:
“空号,也是一种构图。”
声音被取景器吞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