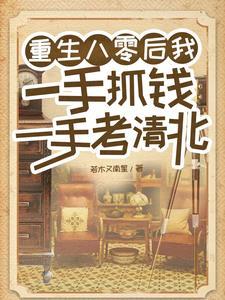紫夜小说>伤心的虫宝宝长大的图片 > 第5章(第1页)
第5章(第1页)
“那你回家等我。”
我起身,拍走衣服上的灰,陈米忽然握住我的手:哪个家?
我没有说话,掌心沾上陈米的手汗,陈米松开我的手:我现在有一个家了,是吗?
这句话说得有一些奇怪。陈米以前也有一个家。可陈米不承认陈运给过他一个家。
陈米问我是与否,我回答“是”。
并非敷衍,我也很想告诉他,其实我也很想要一个家。很小的时候谈过恋爱,太小太小,孤身出国后,无垠浮萍般活着。
亚裔、同性恋、移民,我在五颜六色的小标签里寻找同行人,直到38岁,路一个人走来,以为搭上谁都可以。殊不知不会有人上一趟单程车,上车的旅人未必令我欢欣。
陈运和我不同。陈运领养小孩、和心仪女子结婚又离婚,完成了社会动物的每一道加工工序。
不过陈米长大后,大约十四五岁开始,陈米不再说话,我亦很少见到他了。陈运逐渐不与同事分享儿子的故事。
“怎么不带儿子一起来聚餐?”
“没带就没带呗。”陈运对我翻白眼,“你想见他?”
“以前你总带他。”
“以前他小。”
陈米长大了,有叛逆期,人之常情。
我不做多想,只当陈运不将陈米视为己出,吝惜关爱。
其实视为己出的下场也一样。下楼去超市,走下狭窄的楼道,每次夜晚经过二楼都要听见杨氏夫妇对小杨进行棍棒教育。小杨比陈米小个三四岁。
这栋楼的隔音效果非常差,我在五楼都能听见孩子的哭声。或者六楼那对小夫妻床事。或者七楼,陈米失声前喜欢打开窗户唱歌练声。
那是整栋楼唯一悦耳的声音。
大家都明白隔音差,却在各个角落寻求被人看见的刺激。
几年前我想要搬走,疲于找房不了了之。
我来到小卖部,路过灯箱,抬头望去,天台栏杆后没有了人影。
我心情不错,进入全新装潢的小卖部,拿了一个铁盒装的嘉顿全家桶。从前我不会买全家桶。全家桶对我来说和一人食无任何区别,非要叫这么个惹人厌的名字。
“老板,新装修很干净。”结账,我与老板闲谈,老板是三楼住户,单身汉与单身汉之间存在一种惺惺相惜的默契。
老板咧开嘴,露出金灿灿的门牙,想必赚了许多钱,又装修又换牙。
老板解释说:“之前的门面太小气,小米给我留言,建议我趁冬天好好装一下,春夏旅客多,装修不方便。”
“陈米让你装的?”我想到陈运,“他爸爸……”
“砸我门口石头上了。”老板叹惋,“哎可怜的小孩,现在住你那吧?多多照顾他吧,好在是读大学了,要是还在念中学,又得回青少所、孤儿院了。”
老板不这么讲,我还未发觉,“家”是陈米的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嗯,买饼干给他吃。”我摇一摇嘉顿铁盒,“新的牙很灿烂。”
“你说这个?”老板手指捏一捏门牙,“咍!小米爸爸死在我门口那天,清理现场扫雪的时候捡到一枚大钻戒,以为假的呢,拿去典当,说是真钻石,换了钱赶紧补上我这牙了!”
难怪老板对陈运的死毫不忌讳。
我轻轻羡慕:“你是时来运转啊。”
“诶,哪里哪里。”
真是一个幸运的老板。谁会把钻戒丢雪堆里,偏让他捡到。
老天爷能不能也让我捡一个宝贝……我抬起头,五楼的灯亮起,阳台陈米的衣服和我的衣服交错挂晒。
我好像也捡到了。
陈米喜欢吃旺仔雪饼、嘉顿饼干、草莓巧乐兹。不喜欢吃乐事薯片,认为薯片加工味道太重,吃完后,手指沾满细粉,懒得用纸巾擦,张开手心摊在我面前,让我帮忙。他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零食,眼睛不得空。
陈米好像很喜欢看电视,每一次打开电视,不管放的是什么节目,他都会目不转睛、一丝不苟地看完。
我用湿纸巾仔细地擦他的手指,擦完后帮他剪指甲,做完这些,我告诉陈米:“叔叔预约了心理医生,这周日带你去看看。”
陈米的眼睛终于从电视移动至我的脸,我已经习惯他偶尔流露出来的低沉,黑色的眼瞳不会说话,和他的嘴唇一样,错愕着,微微张大。
“不能拒绝叔叔。”我关掉电视机,“你不喜欢的话,可以不告诉我你不愿意说话的原因,只需要和心理医生沟通就好,我不会介入。”
从周一告诉陈米,到周日带他去心理诊所,陈米每天都要跟我确认:真的要去吗?
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他焦虑紧张,茶饭不思,直到周日结束了第一次心理诊疗,大约三个小时,陈米独自回到家,我正在煮饭,问陈米:“还好吗?医生人怎么样?”
陈米摇头,又点头,意思是“我不好”、“但医生人不差”。
“没关系,慢慢来。”我摸一摸他的额头,刘海下布满密汗。
[可以多慢?]
“多慢都可以。我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像以前一样,唱好听的歌。”我给陈米盛饭,陈米做心理诊疗太累,拌青椒炒肉吃了两大碗。
从那天开始,陈米每一周都会在周日的下午两点自觉前往心理诊所。我在第二个月的最后一周去诊所缴费,接了他一次。
他和心理医生关系不错。那天医生告诉我,陈米很配合她,每一周让陈米记录想要说话的瞬间,他都会分享。
希望陈米多多与我互动,做游戏,激发他说话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