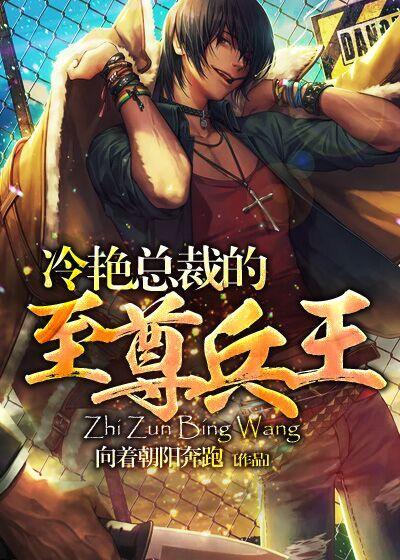紫夜小说>梅魂花的药效 > 第15章(第1页)
第15章(第1页)
回到沈墨兰的公寓,两人相对无言。火灾、威胁、最后通牒……一切都来得太快。
“你可以回去。”沈墨兰突然说,“我不会怪你。”
孟清如猛地抬头:“什么?”
“周世昌说得对。跟着我,你只会受苦。”沈墨兰的声音平静得不自然,“你有才华,有学识,不该为我放弃一切……”
“看着我。”孟清如捧起她的脸,“昨晚的话,我是真心的。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离开你。”
“但那些首饰是你母亲的遗物……”
“物品终究是物品。”孟清如坚定地说,“母亲如果活着,一定会理解我的选择。”
沈墨兰的眼泪终于落下:“那我们怎么办?戏院没了,我连最后一场演出都没了……”
“我们一起想办法。”孟清如擦去她的泪水,“首先得找个安全的地方。周世昌既然敢烧戏院,就敢做更过分的事。”
“去杭州怎么样?”沈墨兰突然说,“我有个师姐在那边开茶楼,经常请戏班演出。我们可以暂时投奔她。”
孟清如点点头:“好,就去杭州。不过在那之前……”她犹豫了一下,“我想再去见父亲一面。”
沈墨兰紧张地看着她:“你要改变主意?”
“不。”孟清如摇头,“但我得让他明白,这是我的选择,与你无关。我不能让你一直背负勾引孟家大小姐的骂名。”
沈墨兰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紧紧抱住了孟清如。两人相拥在狭小的公寓里,窗外阳光明媚,仿佛昨夜的暴雨从未存在过。
但命运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断弦
杭州的清晨比上海宁静许多。
孟清如站在小院的石榴树下,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带着西湖水汽的清新,还有早点摊飘来的油条香气。三个月了,她们在这座城市已经躲藏了三个月。
“清如,过来吃早饭!”沈墨兰的声音从屋里传来,清亮如黄莺。
这是一栋位于清河坊附近的小院,两间正房带个小厨房,月租八块钱。沈墨兰的师姐柳如烟帮忙找的,说是“闹中取静,适合藏娇”。孟清如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时脸红了,沈墨兰却笑得前仰后合。
厨房里,沈墨兰正在盛粥。她穿着简单的蓝布衫,头发随意挽起,额前散落几缕发丝,在晨光中泛着柔和的光泽。桌上摆着刚出锅的葱油饼、一小碟酱菜和两碗白粥——这是她们现在的日常早餐,与孟公馆精致的早点天差地别,孟清如却吃得更加香甜。
“今天我去市场,你想吃什么?”沈墨兰咬了一口葱油饼,含糊不清地问。
“我跟你一起去。”孟清如说。
“不行,太危险。”沈墨兰摇头,“万一被认出来……”
“三个月了,周世昌的人不会一直找。”孟清如坚持道,“再说杭州这么大,哪那么容易碰上。”
沈墨兰还想反驳,孟清如已经伸手抹去她嘴角的饼屑:“我想看你跟鱼贩讲价的样子。”
最终沈墨兰妥协了,条件是孟清如必须戴帽子和眼镜。这三个月来,她们深居简出,沈墨兰偶尔去柳如烟的茶楼唱堂会,孟清如则几乎足不出户,靠给报纸写专栏赚些稿费。虽然清贫,却有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踏实。
杭州的菜市场比上海的小,但同样热闹。沈墨兰熟门熟路地在摊位间穿梭,时不时停下来挑拣蔬菜或讨价还价。孟清如跟在后面,新奇地看着这一切——在孟家,她连厨房都没进过几次,更别说亲自买菜了。
“看,要这样挑茄子。”沈墨兰拿起一根紫得发亮的茄子,“表皮光滑,蒂部新鲜,捏起来有弹性……”她突然压低声音,“两点钟方向,那个戴灰帽子的男人,从鱼摊就跟上我们了。”
孟清如心头一紧,强忍着没回头:“确定?”
“嗯。别慌,我们正常走,去人多的地方。”
两人装作无事发生,继续买菜,但脚步不自觉地加快。拐过一个卖瓷器的摊位后,沈墨兰突然拉着孟清如钻进一条小巷,七拐八绕,最后从一家布店的后门穿出,回到了大街上。
“甩掉了?”孟清如气喘吁吁地问。
沈墨兰回头张望:“应该是。我们赶紧回家。”
小院的门刚关上,两人就瘫坐在椅子上,相视苦笑。
“看来还是不能大意。”孟清如叹气,“可我们总不能躲一辈子。”
沈墨兰握住她的手:“等风头过去就好了。周世昌那种人,新鲜劲儿过了就会转移目标。”
孟清如希望如此,但心里总有种不祥的预感。过去三个月,她通过林宛如了解到,父亲确实冻结了她名下的所有财产,包括母亲的珠宝。周家则对孟家纺织厂进行了“救助”,条件是获得51的股份——这几乎就是吞并。
下午,沈墨兰去柳如烟的茶楼排练。孟清如独自在家,开始整理这段时间收集的资料。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木箱,里面全是关于周家商业活动的剪报和笔记。通过分析这些公开信息,她发现周家的银行资金流向十分可疑——大量现金流入一些空壳公司,然后又转去香港和日本。
“走私……”孟清如喃喃自语。如果能找到确凿证据,或许能反制周世昌的威胁。
傍晚,沈墨兰还没回来。往常这个时候排练早该结束了。孟清如开始不安,正准备去茶楼看看,院门突然被撞开。
柳如烟扶着浑身是血的沈墨兰跌跌撞撞地进来。
“墨兰!”孟清如冲上前,心脏几乎停跳。沈墨兰脸上有淤青,嘴角开裂,最触目惊心的是她的右手——五指扭曲变形,鲜血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