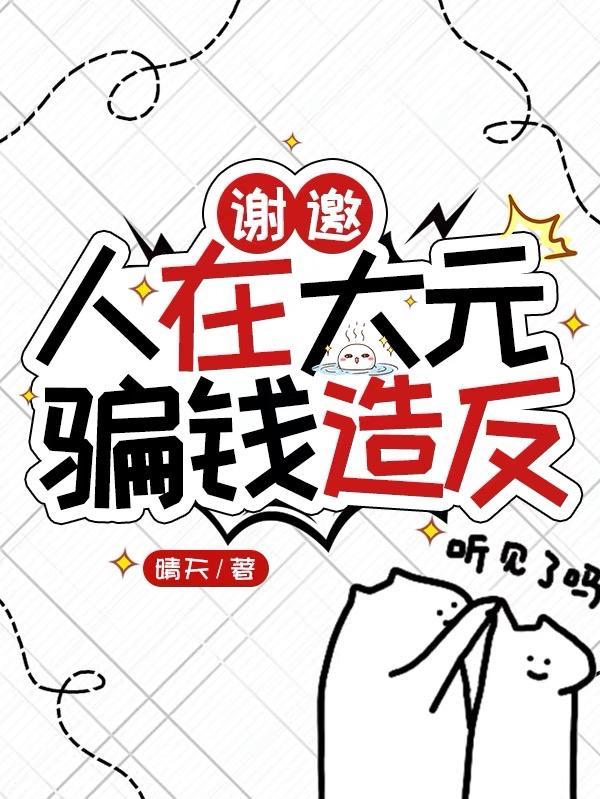紫夜小说>网恋对象是我最恨的竹马怎么办 > 关系缓和(第1页)
关系缓和(第1页)
关系缓和
那场醉酒,像一场失控的山洪,在程曦精心构筑的内心防线上冲开了一道巨大的缺口。
当他第二天在熟悉的宿舍床上醒来时,第一个感觉不是宿醉的头痛,而是排山倒海般的丶几乎让他窒息的羞耻。
阳光透过窗帘缝隙刺入眼帘,也仿佛照进了他记忆中那些破碎而模糊的片段。他记得自己靠在林砚清身上,记得那无法控制的眼泪,记得自己一遍遍含糊地喊着“砚清哥哥”,记得那种近乎幼兽般的丶丢盔弃甲的撒娇和哀求……每一个细节回想起来,都像是一根烧红的针,狠狠扎进他的自尊心。
“我怎麽……怎麽会那样……”程曦把脸深深埋进枕头,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呜咽,身体因羞愤而微微颤抖。
他宁愿林砚清继续用那种冰冷的丶带着恨意的方式对待他,也好过自己如此不堪地丶主动地将最脆弱丶最依赖的一面暴露在对方面前。这比他任何一次在项目组被当衆否定都要难堪百倍。那不仅仅是屈辱,更是一种深刻的丶关于自我掌控力丧失的恐慌。
他一整天都浑浑噩噩,刻意回避着任何可能遇到林砚清的场合,甚至连手机都不敢多看,生怕收到对方带着嘲讽或更进一步威胁的信息。他像一个等待最终审判的囚徒,在忐忑和羞耻中煎熬。
然而,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风平浪静。
林砚清没有来找他,没有发来任何信息,甚至在唯一一次走廊的短暂相遇中,对方也只是如同掠过陌生人般,目光平静地与他擦肩而过,没有停留,没有审视,更没有他预想中的丶因为掌握了新把柄而流露出的任何意味深长。
这种异常的平静,非但没有让程曦安心,反而让他更加不安和……困惑。这不像林砚清的风格。按照他以往的报复逻辑,抓住自己如此大的“失态”,必然会乘胜追击,给予更沉重的打击才对。
就在这种忐忑中,变化开始以一种极其细微丶几乎难以察觉的方式发生。
公开场合,林砚清确实收起了那令人窒息的打压和赤裸裸的无视。
他不再在小组讨论中刻意挑刺,当程曦发言时,他会平静地聆听,偶尔甚至会在他提出某个可行思路时,简洁地附议一句“这个角度可以”,语气客观得听不出任何情绪。
路上狭路相逢,他不再是彻底的空气,那微微的颔首,幅度小得几乎可以忽略,却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程曦心里漾开一圈圈复杂的涟漪。
程曦开始“偶遇”林砚清。在图书馆他常去的靠窗位置,林砚清会“恰好”坐在他对面的桌子;在清晨人迹罕至的教学楼天台,他抱着书本推开门,会发现林砚清正倚在栏杆边,望着远处,听到动静回过头,目光与他短暂交汇,然後无声地离开,留下清冽的气息和程曦骤然加速的心跳。
这些“偶遇”没有任何言语交流,却像一种无声的宣告和试探。
程曦发现自己无法抗拒这种若有若无的靠近。他本该厌恶丶该逃离,但心底某个角落,却因为对方不再充满恶意的目光,甚至那短暂停留的丶不带攻击性的注视,而産生了一丝可耻的丶微弱的悸动。
他告诉自己这只是因为习惯了之前的紧张对峙,现在骤然放松後的不适应,但内心深处,他知道不是。
暗地里的掌控并未消失,反而变得更加精细和……“体贴”。
程曦的课程表和作业截止日期,林砚清了如指掌。他会在某个项目报告提交前夜的九点整,发来一条言简意赅的微信:【参考文献第17页,数据引用有误。】没有称呼,没有问候,直奔主题。
程曦点开自己快要定稿的文档,核对之下,惊出一身冷汗,那个不易察觉的错误若被导师发现,足以让他的成绩降一个等级。
他手指悬在键盘上,挣扎良久,最终只回了一个干巴巴的:【谢谢。】
那边再无回应。
但他知道,林砚清看到了。
生活上的介入更是无孔不入,却披上了“巧合”的外衣。他念叨了好几天想吃却总是售罄的食堂限定甜品,会在某个午後就“刚好”出现在他的书桌上;他因为熬夜着凉有些鼻塞,第二天宿舍的抽屉里就会“多出”一盒副作用很小的感冒药;甚至他随口对室友抱怨了一句旧书包带子要断了,隔天就会有一个款式简洁大方丶质感极佳的新书包,“被错放”在他的床下。
程曦从最初的震惊丶抗拒,到後来逐渐变得麻木。他尝试过无视那盒药,结果第二天发现自己头晕得更厉害,而抽屉里出现了更对症的冲剂。
他也试过把新书包塞进柜子深处,但林砚清下一次在实验室见到他背着旧书包时,那微微蹙起的眉头和虽然没说话却明显不赞同的眼神,让他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反抗是徒劳的,而且……似乎会引来更“周到”的“关照”。程曦悲哀地发现,自己开始习惯了这种无处不在的安排。这让他混乱的大学生活变得异常“高效”和“顺遂”,他不再需要为琐事分心,成绩稳步提升,甚至连气色都好了不少。一种可怕的依赖感在悄然滋生。
“就这样吧,”他对自己说,带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疲惫,“反正也逃不掉……至少现在,没那麽难受了。”他刻意忽略心底那丝因为接受这种“圈养”而産生的自我唾弃。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他们独处的时候。地点依旧是深夜的实验室丶图书馆的僻静角落,或是林砚清那套装修冷清却设施齐全的校外公寓。
但氛围不同了。
林砚清依旧是主导者,他会检查程曦的功课,听他汇报进展。但他的言辞不再尖锐,指导变得更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