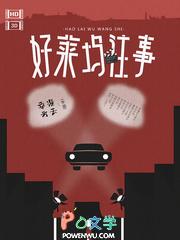紫夜小说>你不是朕的白月光 作者石门之客 > 第59章 第五十九章 我爱你啊(第3页)
第59章 第五十九章 我爱你啊(第3页)
她看见他腰间衣带上有两朵梅花。
像被冷风吹折了。
又吹得失了色。
是她绣的梅花吗?
她不知道。
她看不清了。
两滴泪不期然地落下。
滚到了手上的榛子糕上。
她低下头,捏起了那块湿了的榛子糕,咬下一口。
苦的。
是她很久没有尝过这个样式的榛子糕了吗?为什麽是苦的呢?
很苦,也很涩。
兄长说,喜欢一个人,像饴糖一样甜。
可是,饴糖吃多了,习惯了,一旦不再吃了,吃不到了,就会苦。
吃什麽都会觉得苦。
这就是喜欢吗?
榛子糕还捏在手里。
榛子糕,可……我不是真的喜欢吃榛子啊。
萧珣离开後的翌日,就是正月望夜,不设宵禁。
世子来了书院,请林榆授课,勤勤谨谨地一直学到了入夜。
林鸢就跟着贺季,去淮阳街市上看他一直心心念念的灯和百戏。
流云遮月,灯火迷离。
灯晕之下人头攒动,不时传来阵阵鼓声与高声喝彩,一边有傩戏,一边有角抵。
“要我说,这萧公子离开得真是不巧,这淮阳国望夜里的百戏,是连长安都比不上的。”
贺季边说,边带着林鸢往人最多的地方去。
他嘴上说着遗憾,唇角却咧到了耳梢。
“听说,当今的皇帝不喜欢看戏,如今落马的大司马瞿阳也称这些都是靡靡之音,所以这些从西域来的百戏艺人和幻士去长安的少。都慕着淮阳王的名字,到淮阳国来了。”
他轻啧感慨:“这萧公子也是奇,说是豫章王的公子,岁除元日都不回豫章,看起来是亲人缘薄,来了淮阳国,也不见他与淮阳王还有世子亲近,反而同我们几个厮混在一起。可这次匆忙离开,我问了一声,他却说,是为着一个好几年不见的亲人,所以要赶去长安。”
“我好奇多问了一句,这亲人这麽要紧?那萧公子说,比任何人都要紧。我都疑心自个儿是不是耳拙听错了,应该是‘情人’不是亲人……”
林鸢站在人流里,看着人潮翻涌,轻轻“嗯”了一声。
半晌,问:“这儿演的是什麽戏?”
她踮起脚尖往里看。
“跟我来。”
贺季兴冲冲拉起了林鸢广袖的一个角,在人堆里挤出了一条路。
膀大腰圆的力士两两较力。
是夜无风,但仍是料峭,他们赤着上身,豆大的汗水从那精壮突起的肌肉与经络上滑下。
林鸢有些恍惚,睁大了眼,正要与衆人一道拍手叫好,下一瞬就被挡了视线。
贺季被旁人挤着,正巧被到了林鸢的身前。
他一弯双眼:“阿鸢,我刚听人说桥头有人扮成东海黄公,持刀斗虎,也有漫衍鱼龙,要不要去看?”
索性这里什麽也看不见了,林鸢略一点头。
二人于是往前头买了蜜饵,一边吃,一边慢悠悠地往桥上走去。
贺季看着那映着灯光的江流,讲起了小时候跟着父兄沿着大河,北往上郡,朔方,东往琅琊,东莱,又沿着漳水北上,到过燕国采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