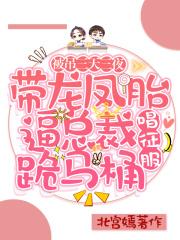紫夜小说>无冕之王指的是谁 > 第32章 天子落难曹营开启迎驾大讨论(第1页)
第32章 天子落难曹营开启迎驾大讨论(第1页)
兴平二年秋,一场席卷整个中原的飓风,自残破的关中呼啸而起,其风眼,正是那位身不由己的年轻天子。
消息如同燎原的野火,以惊人的度传遍九州,最终携着历史的沉重分量,砸入了兖州鄄城的曹营核心:“天子东归!历经李傕、郭汜之乱,汉献帝刘协在国舅董承、白波帅韩暹、以及杨奉、张扬等各怀心思的将领护卫下,九死一生,侥幸逃出已成炼狱的长安!一路颠沛流离,屡遭劫掠,辗转于弘农、曹阳等地,尸横遍野,公卿百官多有饿毙、死于乱军者,最终,这支形容枯槁、如同乞丐般的队伍,狼狈不堪地回到了那片早已沦为焦土瓦砾的故都——洛阳!”
彼时,曹操正与周晏核对新近整理的青州兵籍册,传令兵几乎是踉跄着冲入厅堂,声音因激动和难以置信而尖锐变形。刹那间,空气仿佛凝固了。曹操执笔的手悬在半空,一滴浓墨自笔尖坠落,在竹简上晕开一团巨大的、不合时宜的污迹。周晏则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极其复杂的光芒——既有“果然如此”的历史尘埃落定感,更有对即将掀起的滔天巨浪的清晰预判。
这石破天惊的消息,让整个曹操集团如同被投入滚油的冰块,瞬间炸开了锅。
翌日,议事厅内,门窗紧闭,却关不住那几乎要掀翻屋顶的激烈争论。炭火在铜盆中噼啪作响,映照着每一张或激动、或凝重、或亢奋的面孔。以夏侯惇、曹洪为代表的武将集团情绪最为高涨。
夏侯惇霍然起身,独眼因兴奋而精光四射,声若洪钟,震得梁上微尘簌簌而下:“大哥!还有何可议?!天子蒙尘,流离失所,正需我等忠臣良将奋起护驾!此乃上天赐予的良机,千载难逢!正可借此大义名分,号令天下,征讨不臣!当立刻尽起精锐,西向洛阳,迎奉天子!”
曹洪紧接着站起,他性子更急,挥舞着手臂,声音激昂:“元让兄所言极是!什么袁绍、袁术,什么刘备、吕布,不过割据之臣!只要天子在手,主公便是擎天保驾之臣,大义名分在手,看谁还敢说我们是僭越!兵!迟则生变,若被他人抢先,悔之晚矣!”一众将领纷纷附和,甲胄铿锵,战意高昂,仿佛下一刻就要拔营西进。
然而,另一派声音同样不容忽视。以部分文臣及地方实务官吏为代表,他们面露深深的忧色,显得冷静乃至保守。
一位掌管粮秣的主簿颤巍巍出列,声音带着忧虑:“主公,诸位将军,还请三思啊!洛阳如今是何光景?宫室尽成焦土,街巷荆棘丛生,饥民相食,如同鬼域!且关中各路兵马混杂,李傕、郭汜虽暂时退去,其狼子野心未死,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此时迎驾,无异于将一个巨大的、嗷嗷待哺的包袱背在身上!需耗费多少钱粮?需动用多少兵力护卫?更遑论天子身旁,那些公卿大臣,个个眼高于顶,门第观念根深蒂固,若迎至兖州,他们指手画脚,干涉军政,届时是主公听他们的,还是他们听主公的?只怕请神容易送神难,反受其制啊!”
这番话如同冷水泼入沸油,引了更多关于实际困难的讨论。有人提及兖州新定,青州兵未稳,不宜远征;有人担心迎驾会过早暴露实力,成为众矢之的。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厅内气氛愈胶着。
曹操端坐主位,面色沉静如水,手指依旧无意识地、一下下敲击着案几,目光却如同深潭,在麾下每一位核心谋士的脸上逡巡,捕捉着他们最细微的神情变化。他需要的不只是群情激昂,更是洞穿迷雾的远见。
终于,侍中守尚书令荀彧动了。他整理了一下衣冠,越众而出,并非简单地拱手,而是对着曹操,极其郑重地长揖到地。当他抬起头时,平日温润如玉的面容上,此刻却因激动而泛着红光,那双清澈的眼眸中,燃烧着理想与信念的火焰。
“主公!”荀彧的声音清越而坚定,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瞬间压过了堂内的嘈杂,“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丧,而天下归心!此乃万世不易之理!如今天子蒙尘,颠沛流离,四海之内,忠义之士无不忧心如焚,黎民百姓翘以盼王师!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此乃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此乃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此乃大德也!若持疑而不往,一旦他人——无论是袁本初,还是其他什么人——抢先一步,届时,主公虽欲尽忠,亦无门矣!夫权宜之策,在于掌握主动,岂能因噎废食,畏惧艰难而错失此不世之业乎?!”
他引经据典,慷慨陈词,将迎奉天子拔高到了顺天应人、奠定王业根基的战略高度。每一个字都如同重锤,敲打在曹操的心坎上。
程昱紧随其后,他依旧是那副冷峻的面容,但语气中的决绝与荀彧的理想主义交相辉映:“文若所言,乃万世之基,绝非虚言。迎天子,非仅为博取虚名,实乃收取天下之实利。名分既正,则征伐自如,檄文所至,莫敢不从。届时,招募贤才,广纳流民,皆名正言顺。些许钱粮消耗,与所得之巨大优势相比,何足道哉!当断则断,不可效仿袁本初之优柔!”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曹操微微颔,荀彧的大义与程昱的务实,如同车之两轮,让他心中的天平已然倾斜。但他依旧将目光投向了那对年轻的谋士组合,尤其是总能带来意外之见的周晏:“奉孝、子宁,大势已明,然具体方略,尔等何以教我?”
郭嘉早已放下了手中把玩许久的玉佩,那双灵动的眸子此刻闪烁着洞悉一切的光芒,仿佛已经看到了数年乃至数十年后的格局。他坐直了身子,虽然姿态依旧带着几分随意,但语气却异常清晰锐利:
“主公,迎,必须要迎!此乃定鼎之基,毋庸置疑。”他先定下基调,随即话锋一转,“然则,如何迎,却大有讲究。文若先生言其利,仲德先生言其要,嘉则言其法。洛阳残破,几无屏障,绝非定都之地。若将天子百官直接迎至兖州州治,确如方才诸公所虑,易生掣肘,且目标太大,易招致四方围攻。”
他伸出手指,在空中虚点,仿佛在勾勒一幅宏大的蓝图:“嘉以为,不若另择一处地处中原腹地、水陆便利、易守难攻,且最关键的是——便于主公全然掌控之新城,作为天子驻跸之所,亦即新的都城。譬如……颍川之许县?”他顿了顿,观察了一下曹操的反应,继续道,“此地西接洛阳,东连兖豫,北望河内,南临荆襄,地势平缓却非无险可守,更兼土地肥沃,利于屯垦。且,非朝廷旧都,无盘根错节的旧势力,一切皆可从新规划,便于主公施为。”
“再者,出兵需快!以精骑锐卒,星夜兼程,务必抢在袁绍反应过来之前,率先抵达洛阳,掌控局面。但姿态需做足,显是忠心护驾,雪中送炭,而非强兵挟持,授人口实。此中分寸,至关重要。”
压力给到了周晏。他正努力消化着这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巨大转折,听到曹操询问,下意识地揉了揉因连日处理文书而有些胀的额角。迎奉天子……他知道这是曹操霸业乃至整个三国历史的关键一步,利弊都极其分明,操作更是如履薄冰。他整理了一下被郭嘉宏大构想激荡的思绪,尽量用符合这个时代逻辑、又能体现自身特质的方式表达:
“将军,”周晏的声音依旧带着点慢吞吞的味道,但内容却条理分明,“文若先生所言乃正道沧桑,奉孝之策乃机变奇谋,皆切中要害。天子,终究是天下共主,其象征意义,在当今乱世,非但未曾减弱,反而因其蒙难而更具凝聚力。迎奉天子,于大义名分,于招揽四方贤才,于未来征伐不臣,皆有莫大好处,确如文若先生、仲德先生所言,乃根本之策。”
他话锋一转,开始切入务实的操作层面:“至于奉孝所虑之耗费与掣肘……晏以为,其策甚妥。择新城而都,如许县,既可避开洛阳废墟与复杂旧势力,又能将中枢置于我军势力辐射之内,实为上选。此外,于具体安置上,”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迎奉之后,对天子本人,需极尽臣礼,供奉周全,以示尊崇,此乃安定人心之基;然对于随行之公卿百官,则需……嗯,‘量才录用’,确有实学者,可委以相应事务;而无甚才干、只知清谈或摆弄权术者,则不妨‘荣以虚位’,厚其俸禄,尊其名号,却不必使其干预核心机要。总而言之,军政钱粮、人事任免等实权,仍需牢牢掌握在将军及其信任的股肱之臣手中。简而言之……尊天子以令不臣,握实权而避虚文。如此,或可最大限度获取其利,而规避其弊。”
他这番话,没有荀彧的理想主义激情,没有郭嘉的天马行空,也没有程昱的冷硬决绝,却如同一位技艺精湛的工匠,将前三人提出的战略蓝图、奇谋构想与风险警示,糅合、打磨,补充上了最为关键、也最需谨慎处理的内部操作细节,使其变得清晰、可行。
曹操听完麾下这四位风格迥异、却智慧群的谋士——理想之锚荀彧、现实之刃程昱、奇策之锋郭嘉、务实之砥周晏——的见解,胸中豁然开朗,再无半分犹豫。他猛地从主位上站起,身躯挺拔如松,一股睥睨天下的气势油然而生。
“诸公之论,字字珠玑,深得吾心!”曹操声若雷霆,斩钉截铁,目光锐利如鹰,扫视全场,“天子有难,为人臣者,岂能坐视不顾,畏缩不前?!迎驾之事,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他不再给争论留下任何空间,一连串的命令如同疾风骤雨般下达:
“曹仁、乐进听令!命你二人,即刻点齐一万精兵,多为骑兵,携带部分粮草医药物资,星夜兼程,赶往洛阳护驾!要之务,确保天子与公卿安全,肃清洛阳周边威胁,并详细探查道路情形、洛阳残破程度及粮草储备!”
“荀彧、程昱听令!统筹调度兖州粮草物资,全力保障大军后勤!同时,着手规划迁都许县事宜,勘定地址,筹备建材,招募工匠,此事关乎未来根基,务必周密!”
“郭嘉、周晏听令!随我坐镇鄄城,统筹全局,密切关注袁绍、袁术、刘表等周边诸侯动向,若有异动,随时献策应对!”
“诺!”堂下文武,无论先前持何意见,此刻见主公意志已决,且策略周详,皆轰然应命,声震屋瓦。一股昂扬的斗志与肩负历史的使命感,在每个人心中升腾。
喜欢三国:无冕之相请大家收藏:dududu三国:无冕之相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