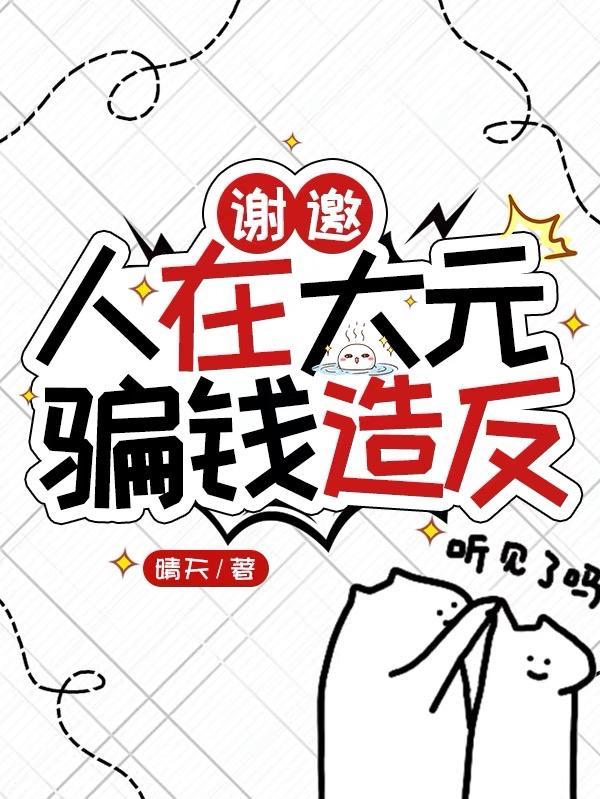紫夜小说>大衍宏开光禹范;知非伊始学蘧年 > 第31章 沈砚答应了混入黔南关(第2页)
第31章 沈砚答应了混入黔南关(第2页)
沈砚点点头,挑起担子,率先走出破庙。晨光穿过树梢洒在他身上,挑担的身影融入乡间小路的晨雾中,朝着黔南关的方向走去。一场关乎萧策生死、搅动边境风云的潜入计划,就此悄然展开。
三日后清晨,望云破庙笼罩在薄霜中。庙门半掩,蛛网挂在残破的窗棂上,地上的枯草沾着白霜,远处的山峦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十五名岭南士兵已等候在此,个个身着洗得白的布衣,面容被尘土遮去几分,腰间藏着铁钎与迷烟,双手不安地绞着,却没人敢出声。
脚步声从庙外传来,沈砚挑着杂货担子走进来,竹笠檐压得极低,遮住了眉眼。他身着青布短打,裤脚卷起,露出沾着泥点的脚踝,肩上的担子一晃,铜铃铛“叮铃”作响,活脱脱一个赶早路的货郎。
“都到齐了?”沈砚放下担子,摘下竹笠,目光扫过众人,“记住,从现在起,我们不是世子与士兵,只是一群讨生活的市井人。”他抬手示意,墨书从门外拎进十五个包裹,“各自取自己的装束,换上后检查一遍,不准留任何破绽。”
岭南士兵们立刻上前,拆开包裹:两名身材高大的换上沾着泥污的车夫服,腰间别着旧马鞭,裤腿上还故意蹭了些草屑;三名瘦削的穿上带补丁的流民装,头揉得散乱,手里攥着破碗,脸上抹了点灰,看着就像饿了几天的乞丐;四名手上有老茧的换上蓝布修补匠服,工具袋里装着锉刀、锤子和几块旧木料,工具上还沾着木屑;剩下六名则换上小商贩的粗布衣裳,挑着空竹筐,筐里垫着旧布,看着像是要去集市进货。
沈砚逐一检查,指着一名流民装扮的岭南士兵的衣襟:“这里补丁缝得太整齐,市井人的补丁都是歪歪扭扭的,拆开重缝。”又看向一名车夫装扮的士兵:“马鞭的穗子太新,用石头磨旧些。”直到确认每个人的装扮都毫无破绽,他才点头:“出,按之前排好的顺序,前后拉开五十步距离,装作互不相识。”
他挑起杂货担子走在最前面,竹笠檐遮住半张脸,脚步不急不缓,挑担的姿势自然得仿佛做了十几年货郎。出了破庙,晨雾渐散,乡间小路蜿蜒向黔南关延伸,路面铺着碎石,马蹄印与车辙交错,两旁的麦田里,偶尔有早起的农夫弯腰劳作,远远瞥见他们,只当是赶早进城的生意人,并未在意。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午时过后,黔南关的轮廓终于清晰起来。城门巍峨,由青黑色巨石砌成,高达三丈,城门上方“黔南关”三个大字刻在匾额上,字体遒劲,被岁月磨得有些光滑。城门两侧各站着四名卫兵,身着银甲,手持长枪,腰间佩刀,目光锐利地扫视着进城的人,城门下还设着两道关卡,几名士兵正仔细盘查着过往行人的行李。
沈砚放缓脚步,走到关卡前,放下担子,脸上堆起憨厚的笑容,从怀里摸出几枚碎银,递向一名领头的卫兵:“官爷,辛苦辛苦,小的是走街串巷的货郎,进城卖点杂货,您多担待。”
卫兵斜睨他一眼,接过碎银掂了掂,语气不耐烦:“担子打开看看。”
沈砚连忙掀开担子上的粗布,露出里面的针头线脑、胭脂水粉,笑着说:“都是些小物件,不值钱,您瞧瞧。”卫兵伸手翻了翻,指尖划过杂货堆,没现异常,又看了看沈砚的装束,确实是个普通货郎,便挥挥手:“进去吧,规矩点,别闹事。”
“哎!谢谢官爷!”沈砚连忙挑起担子,铜铃铛轻响着走进城门。进城后,他并未停留,沿着青石板路往前走,眼角的余光瞥见身后的岭南士兵们正逐一接受盘查:车夫装扮的士兵装作赶车累了,骂骂咧咧地递上碎银;流民装扮的士兵缩着身子,怯生生地低着头,被卫兵推搡着进城;修补匠装扮的士兵则大声吆喝着“修补桌椅、锔碗锔盆”,吸引了卫兵的注意力,顺利过关。
待所有人都进了城,沈砚挑着担子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放下担子,抬手摸了摸耳朵。片刻后,岭南士兵们陆续赶来,一个个压低声音汇报:“世子,城门卫兵每半个时辰换一次岗,左右各四人,还有两名骑兵在城门两侧巡逻。”
“城南有个集市,人多眼杂,适合打探消息。”
“城墙上有士兵走动,每隔十步就有一个哨位。”
沈砚点点头,从担子底层摸出空白纸和炭笔,快画了个简易的城门布局图,标注上巡逻时间和哨位位置:“现在分散行动,车夫去城西的车马行,打探城内外的交通路线和卫兵盘查规律;流民去城北的贫民窟,那里鱼龙混杂,最容易听到消息;修补匠去帅府附近的街巷,借口修补东西,观察帅府的守卫情况;小商贩去城南集市,留意有没有士兵闲聊,打探地牢的大致位置。”
他将炭笔收好,目光严肃:“记住,只听只看,不准问太多,遇到卫兵盘问,就按之前教的话术应对,酉时准时到城南老槐树汇合,不准迟到。”
“是!”岭南士兵们齐声应道,各自整理了一下装束,悄然退出小巷,融入了黔南关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沈砚挑起担子,也慢悠悠地走出小巷,铜铃铛的声响混在市井的喧嚣里,无人知晓,一场精密的营救计划,已在这座重兵把守的关隘中,悄然铺开。
酉时的黔南关,夕阳将青石板路染成暖金色,城南老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树底下摆着个卖凉茶的摊子,摊主正慢悠悠地扇着蒲扇。沈砚挑着货郎担子,装作歇脚的模样靠在树干上,竹笠檐遮住眉眼,眼角却留意着往来行人。
先是两名车夫装扮的岭南士兵走来,手里拎着空酒壶,装作刚从酒馆出来,走到树后低声道:“世子,城西车马行的老板说,城内外只有正门和北门的密道能进出,北门密道通往后山,每晚亥时关闭,卫兵盘查比正门松些,换岗是一炷香一次。”
话音刚落,三个缩着身子的“流民”也凑了过来,其中一个手里还攥着半个啃剩的窝头,声音压得极低:“世子,城北贫民窟的老乞丐说,城西北角靠近城墙根有个大牢,就是关押重犯的地牢,外面围了两层木栅栏,还拴着十几条狼狗,每刻钟就有一队卫兵巡逻,夜里更严。”
他顿了顿,补充道:“我们还听到两个换岗的卫兵闲聊,说地牢里关了个‘叛军小头领’,赵王爷下令,除了送饭的,任何人不准靠近,送饭的都是正午时分,由两名卫兵跟着。”
正说着,四名穿着蓝布衣裳的修补匠也赶来了,其中一个肩上还扛着没修好的木盆,脸上沾着木屑:“世子,我们在帅府东侧的街巷吆喝时,被帅府的卫兵叫去修后院的木栅栏。帅府里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换岗时间是半个时辰一次,从帅府后门出来,往西北走约莫两里地,就是地牢的方向,沿途有三个哨卡,都要验腰牌。”
“我还看到,地牢的入口在地面下,盖着块厚重的青石板,上面有四个卫兵守着,石板旁边有个小房子,是卫兵的值班室。”另一个修补匠补充道,手指在地上悄悄画了个简易的入口轮廓。
沈砚点点头,刚要说话,最后六名小商贩装扮的士兵也挑着空竹筐赶来,其中一个道:“世子,城南集市的菜贩说,最近城里查得严,尤其是陌生人,夜里戌时过后就不准在街上走动,否则会被当成奸细抓起来。我们还看到,城墙上的哨位每十步一个,都架着弓箭,夜里会点火把,能照到城墙下三丈远的地方。”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沈砚抬手摸出炭笔和纸,借着树影快勾勒:“地牢在西北,入口是青石板,外层木栅栏+狼狗,内层卫兵+值班室,巡逻每刻钟一次,送饭在正午。帅府到地牢有三个哨卡,需要腰牌。北门密道亥时关闭,盘查较松。”
他画完,将纸折好塞进怀里,目光扫过众人:“今晚先歇着,明早我去地牢附近探探具体的布防,流民和小商贩去摸清北门密道的位置,修补匠再去帅府附近看看,能不能弄到一张哨卡的腰牌样式,车夫去打听清楚亥时密道关闭前的最后一波盘查规律。”
“记住,明晚酉时还在这里汇合,无论有没有收获,都必须准时到,不准单独行动。”沈砚语气严肃,竹笠下的眼神锐利如刀。
众人齐声应下,各自整理了一下装束,装作互不相识的模样,渐渐融入了暮色中的市井人群。沈砚挑着货郎担子,慢悠悠地走向城西的客栈,担子上的铜铃铛轻轻作响,在渐暗的天色里,显得格外不引人注目。而他怀里的那张草图,却藏着能搅动整个黔南关的秘密。
次日天刚蒙蒙亮,沈砚便挑着货郎担子出了客栈,青布头巾压得更低,筐里的杂货被重新整理了一番,最外层摆着几捆粗麻绳和一把长柄扫帚——这是他特意准备的“幌子”,借口给附近住户送货,好靠近地牢区域。
黔南关的清晨还带着凉意,西北方向的街巷比城南冷清许多,两旁多是低矮的民房,偶尔有早起的妇人开门泼水,见了沈砚这货郎,也只是瞥一眼便缩回屋中。沈砚挑着担子,脚步看似随意,实则每一步都在丈量距离,眼角的余光死死盯着前方两百步外的那片区域——那里围墙高耸,墙头插着尖刺,隐约能听到狗吠声,正是地牢所在。
他没有直接靠近,而是拐进旁边一条小巷,放下担子,装作整理杂货的模样,实则借着巷口的拐角,仔细观察:地牢的围墙是夯土混着碎石砌成的,高约两丈,墙外拴着十二只狼狗,分成三圈,每圈四只,正趴在地上打盹,旁边有个小土屋,应该是喂狗的卫兵住处;围墙正中间是一块巨大的青石板,约莫丈许见方,石板四角各站着一名卫兵,腰间佩刀,手里端着长枪,目光警惕地扫视四周;青石板西侧的值班室里,坐着两名卫兵,一人正低头擦拭兵器,另一人靠在椅背上打盹,嘴角还流着口水。
沈砚看了半炷香,摸清了巡逻规律:每刻钟有一队五人的卫兵从值班室出来,绕着围墙走一圈,巡逻时会顺便检查狼狗的锁链,而石板旁的卫兵换岗时间是一炷香零一刻——换岗时,老卫兵会先退出石板范围,新卫兵再上前接手,中间有大约半盏茶的空档,石板旁会暂时无人看守。更关键的是,他现喂狗的卫兵每天辰时三刻会提着食桶出来喂狗,此时狼狗的注意力全在食物上,对周围的动静最不敏感。
记清这些细节,沈砚挑起担子,装作要离开,刚走两步,却见一队巡逻卫兵迎面走来,他立刻放下担子,拿起长柄扫帚,弯腰清扫巷口的落叶,头埋得极低。
“干什么的?”领头的卫兵厉声喝问,长枪尖几乎顶到他的脊梁。
沈砚连忙堆起笑容,抬头时露出半张憨厚的脸:“官爷,小的是货郎,给前面张大户家送扫帚和麻绳,这就走,这就走!”说着,他从怀里摸出两枚碎银,悄悄塞给那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