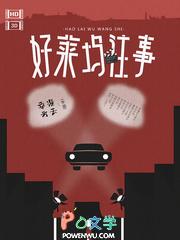紫夜小说>快穿炮灰觉醒gl > 第85章 我像是那麽善解人意的人吗(第2页)
第85章 我像是那麽善解人意的人吗(第2页)
赵雪衣神色一凛,立刻回道:“探马来报,段逐风已被成功阻于陇西道一线,但此人用兵如神,我们设下的几处障碍恐拖不了他太久。他麾下‘风字营’精锐,战力彪悍,若让其突破防线直扑京城,虽不至于扭转乾坤,但也是个大麻烦。”
萧怀琰沉吟片刻,“段逐风是忠臣,更是聪明人。他如今最大的软肋,不是陇西道的天险,而是这京城皇宫里,他誓死效忠的旧主。”
赵雪衣立刻领会:“殿下的意思是……攻心为上?”
“不错。”萧怀琰淡淡道,“派人将已‘自愿’居于深宫丶安然无恙的消息,‘不小心’透露给段逐风的探子。再暗示他,若他轻举妄动,刀兵一起,最先遭殃的,恐怕就是他那旧主的安危。”
现在的他的确做不到对沈朝青动手,但不代表旁人会信。
赵雪衣抚掌,眼中露出钦佩:“妙!段逐风投鼠忌器,必然不敢再贸然强攻!届时我们再以谈判之名,行拖延之实,待殿下彻底掌控京畿周边,整合完毕,段逐风孤军深入,便不足为惧了!”
“不止如此。”萧怀琰眼神幽深,“派人接触段逐风副将,许以高官厚禄。段逐风对沈朝青忠心耿耿,可他手下的人,未必个个都想陪着。”
赵雪衣深深一揖:“殿下深谋远虑,臣即刻去办!对了,昭王那边马上就要来晋国了。”
“那正好。”萧怀琰面无表情,吐出的字眼却极尽冷血,“同归于尽,岂不美哉?”
翌日清晨,沈朝青在一阵压抑的头痛和胸腔的闷痛中醒来。
寝殿内光线昏暗,安静得可怕。
殿门被轻轻推开,一个面生的小太监低着头,端着洗漱用具走进来,动作拘谨惶恐。
沈朝青撑着手臂坐起身,盯着他瞧了一会儿。
林绶,先前帮他照顾小狼的宫人,看来晋国灭後他便投了萧怀琰。
“福安呢?”
林绶动作一僵,手里的铜盆差点没拿稳,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声音发颤:“回丶回陛下……福公公他,昨日殁了。”
沈朝青的动作顿住了,仿佛没听清,又仿佛听清了却无法理解:“……殁了?”
那个啰嗦又忠心,最後关头还想护着他逃走的老人,没了?
林绶伏在地上,不敢擡头,声音带着哭腔:“是福公公昨日拼死想闯进宗庙寻陛下,但丶但辽人得了命令,不准任何人进去,他丶他就在外面……不停地磕头……头都磕破了……流了好多血……拉都拉不住……最後就……就……”
他也没有想过人能磕死。当时满地都是血,福安被当个死狗一样的拖出去,蜿蜒出一片猩红,触目惊心。
见到他的惨状,不管是因为什麽,都瞬间击溃了晋国宫人的心理防线。
那些原本有些傲骨的人全都跪了下来,抖如筛糠,“愿归顺殿下!”
後面的话,林绶说不下去了。
沈朝青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搭在锦被上的手,指节一点点攥紧,用力到泛白。
口腔内壁被他自己咬破,弥漫开一股浓郁的血腥味,苦涩异常。
萧怀琰,这才是你真正的手段。借着杀福安,威慑宫人,接下来,是杀谁?段逐风吗?
良久,沈朝青才极其缓慢地松开紧咬的牙关,突然莞尔一笑,笑意不达眼底,“我要见你们太子。”
林绶吓了一跳,为难地擡头:“这,陛下,您别为难奴才,殿下他军务繁忙。”
沈朝青看着他,脸上的笑意加深了些,却莫名让人心底发寒。
他手腕翻转,一柄小刀按在了林绶的脖子上,瞬间划出血线。
林绶吓得魂飞魄散,“陛下!陛下您要做什麽?!”
“我像是那麽善解人意的人吗?”沈朝青脸上依旧带着那抹让人毛骨悚然的微笑,声音轻柔:“带路吧,不带路,你还是要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