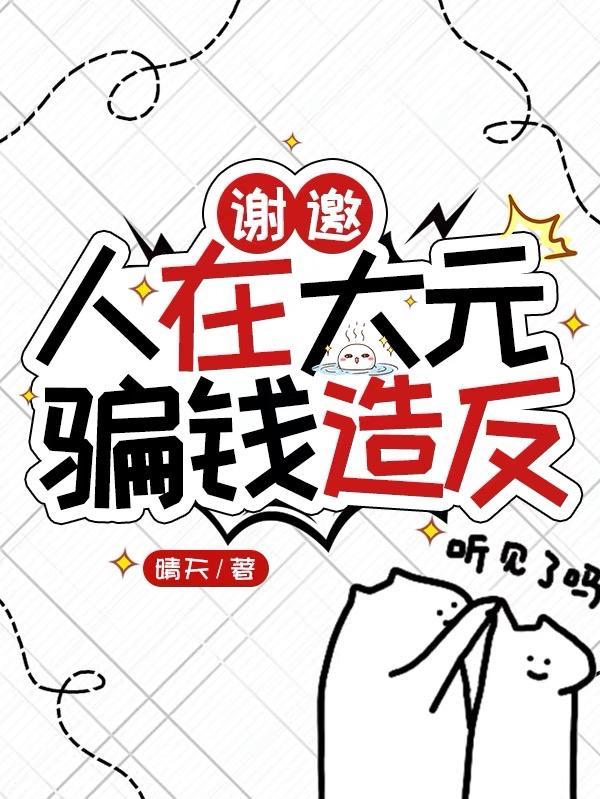紫夜小说>雪夜相拥后是晴天是什么歌 > 眼波流转间的沦陷(第1页)
眼波流转间的沦陷(第1页)
眼波流转间的沦陷
鲁南的秋老虎比江沪黏人得多,明明已过了处暑,日头晒在身上还是燎得慌。蝉鸣拖得有气无力,趴在老槐树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叫。
当年沈宁攥着刚领的蓝白校服站在高二(三)班门口,後颈的汗顺着衣领往下滑,把里头的白T恤洇出一小片湿痕。
“哎,听见没?说话软乎乎的,像含着块糖似的。”
“可不是麽,转来咱这小地方,脚上还蹬着耐克呢。怕不是来体验生活的?”
窃窃私语像撒了把小石子,一下下砸在背上。
他刚攥着书包带往前挪了半步,小声问“侬好啊~请问……”,尾音还带着点江沪特有的软糯调子。
前排几个正转着笔的男生就“嗤”地笑出了声,其中一个还故意学他:“侬好呀~”
沈宁捏书包带的指节泛了白。
来之前他就知道会这样。
尽管心里还有些不适应,但既然已经来到这里,就会好好努力融入,尽量让妈妈少些牵挂。
母亲和父亲当年的婚事,听说在姥姥家那边闹得很是沸沸扬扬,几乎是和家里翻了脸才成的。
因为妈妈当年是未婚先孕,鲁南这边传统思想比较严重。当年出嫁,就姥姥陪嫁了几床被子。
姥爷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一直不让妈妈回家。等沈宁周岁了,姥姥想的很,姥爷才同意妈妈逢年过节,带着沈宁回来一趟。
前几年姥爷走了,家里就剩姥姥一个人守着鲁南的老宅子。这两年她身子骨越发不如从前,前年摔了一脚,一到阴雨天就疼得站不直。
打那以後,母亲几乎每周末都要攥两天时间,坐周五晚上的火车往鲁南赶,周日晚上再匆匆回江沪,周一早上直接去上班。
光路上来回折腾十几个小时,就为了给姥姥拆洗拆洗被褥丶买些常用的药,再做顿热乎饭,陪着说说话。
妈妈不是没提过,想把姥姥接到江沪一起住,可姥姥总摇头,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姥姥只有守着老宅丶街坊邻居,还有院子里那棵姥爷种的石榴树,才睡得踏实。
母亲拗不过她,只能这样两头跑,眼底的红血丝就没断过。
好在现在她们都回来了,沈宁妈妈总算能好好尽孝了,照顾姥姥也方便了些。
可姥姥是个闲不住的性子,哪怕腿脚不利索,也天天拄着拐杖往外跑。
清晨先去老宅後面的小菜园,侍弄她的小菜园,浇水施肥。在去前院喂喂鸡鸭鹅。
忙完之後中午回来自己生火做饭,饭後午睡一下,睡醒之後下午会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口,和路过的老邻居唠唠家常。
谁劝都不听,说“动一动才舒坦,躺着反倒要出毛病”。
母亲为了沈宁上学方便,在学校旁边租了个带小院子的房子。又想着多挣点钱,便在菜市场口盘下了个小摊位,专做她最拿手的菜煎饼。
每天天不亮,母亲就先骑着自行车往老宅跑,帮姥姥把一天吃喝弄好,衣服洗好。叮嘱几句“别走远”“按时吃药”,才匆匆赶回来准备出摊。
回到出租屋,她手脚麻利地摊煎饼丶切菜丶配料,准备出摊的东西。等午饭前,她的菜煎饼摊就在菜市场支棱起来了。
沈母先在鏊子上倒些油,提前备好的煎饼摊在鏊子上,在煎饼上倒个搅匀的鸡蛋。在倒上顾客选好,调好口味的菜,在铺上一层煎饼。
等到两面的煎饼摊成金黄酥脆之後,卷起来,包在提前准备好的纸袋里,递到顾客手里。
暖乎乎的香能飘出老远。
从清晨的老宅到喧闹的菜市场,从姥姥的粥碗茶饭,到顾客的菜煎饼。
母亲的日子就围着这两头转,脚步匆匆,却从没抱怨过一句。
沈宁看着母亲鬓角悄悄冒出来的白头发,突然觉得,一阵心疼。
母亲总攥着皱巴巴的票子念叨“妈能挣钱,你好好念书就行”……
沈宁回过神来,看了一眼自己脚上的鞋。是他妈妈去年过生日时候给他买的。
回来的时候随手拿了两双。没想到引起这麽大的关注。
正僵着没处躲,後桌突然传来“咚”一声闷响。
是个高个子男生,校服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小臂上被晒出的麦色,他刚把桌肚里的篮球捞出来,胳膊肘顺带撞了下前排那个笑最欢的男生後背。
“笑什麽?”男生声音有点哑,像砂纸磨过老木头,“嘴里塞鸡毛了?”
前排男生悻悻回头,看清是姜野,嘟囔了句“没笑啥”,赶紧转了回去。
教室里的嗡嗡声瞬间矮了大半,连窗外的蝉鸣都像是轻了些。
沈宁愣了愣,还没来得及说句谢,姜野已经拉开他旁边的椅子坐下,随手把篮球塞回桌底,眼尾扫过他手里的校服:“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