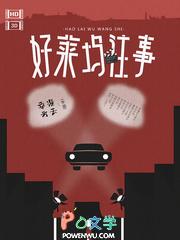紫夜小说>雪夜相拥图片 > 被迫别离苦难生(第2页)
被迫别离苦难生(第2页)
他骂他爸狠心,为了所谓的“体面”就能把亲儿子扔进这种鬼地方。骂这暗无天日的牢笼根本不是人待的。
可看守的人眼皮都没擡一下,只粗暴地往他嘴里塞了块污秽的破布,腥臭气呛得他直反胃,下一秒就被人攥着胳膊往墙上猛撞。
“咚”一声闷响,後脑勺结结实实磕在冰冷的水泥墙上,钝痛瞬间炸开,像有无数根针往脑仁里扎。
姜野眼前猛地一黑,金星乱冒,恍惚间听见有人在他耳边啐了句:“犟种就得这麽治,治到你服软为止。”
里面的日子根本没个章法。
天还没亮透,公鸡还没打鸣,就得被看守的哨声拽起来,在院子里冻得硬邦邦的空地上站成排,扯着嗓子念那些狗屁不通的“悔过书”。
纸页上的字歪歪扭扭,全是些“我不该有悖伦常”“我要痛改前非”的鬼话,谁要是声音小了丶念得慢了,立刻就会被两个膀大腰圆的看守拽出来,在院子中央罚站。
风跟淬了冰的刀子似的,刮在脸上又冷又疼,冻得人鼻尖发红丶眼泪直流。可就算站到双腿发麻丶脚踝僵硬得像灌了铅,也没人敢动一下。
姜野被罚过两次,一次站了整整一上午,等被允许回屋时,他的腿已经麻得没了知觉,是拖着两条腿挪回去的,夜里膝盖疼得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只能咬着牙硬扛。
饭更是难以下咽。
糙米饭糙得硌嗓子,混着没淘干净的沙粒,配菜永远是寡淡的咸菜,偶尔能在盆底见着点油星子,就得抢着往嘴里扒。慢一步,碗里就只剩些结了块的硬疙瘩,嚼起来像啃石头。
姜野起初硬气,宁肯饿肚子也不碰那些东西,可饿了两天,胃里就跟揣了团火似的,烧得他五脏六腑都疼,最後实在撑不住,只能捏着鼻子扒了两口。
他不能倒下,他得活着出去,他还没见到沈宁呢。
最熬人的是那些所谓的“治疗”。
他被关进不见天日的小黑屋,里面只有一张冰冷的铁床,墙角结着蛛网,空气里飘着霉味。
看守的人隔上半个钟头就进来一趟,手里捏着电棍,面无表情地问:“知道错了吗?”
他不吭声,对方就把一盏强光灯怼到他脸前,惨白的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眼皮被刺得生疼。
就这麽熬到後半夜,脑袋里嗡嗡作响,像有无数只蜜蜂在里头打转,可他偏要咬着牙撑着。
他没错,喜欢沈宁不是错。
有次被硬灌了药,昏昏沉沉睡了两天两夜,醒过来时浑身软得像没了骨头,连擡手的力气都没有。
他趴在铁床上,看着墙上自己歪歪扭扭的影子,瘦得脱了形,却依旧梗着肩颈。
恍惚间想起沈宁总笑他:“姜野你站着都像棵树,直愣愣的。”那时沈宁的指尖轻轻戳着他的胳膊,带着温温的暖意,如今想起来,心口又酸又软。
姜野第三次被带去做电击治疗时,脚刚踏上治疗室的台阶,胃里就一阵翻江倒海。
他清楚地知道将要面临什麽。
上一次的疼还刻在骨头上,可走到房门前,那股深入骨髓的恐惧还是攥紧了他的心脏,让他浑身发僵。
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把他按在冰冷的铁椅子上,粗硬的皮带一圈圈捆住他的手腕丶脚踝和腰腹,勒得他喘不过气。
冰冷的电极片贴上他的手腕丶太阳xue和腹部时,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每根寒毛都因预知的痛苦而竖了起来。
对面的屏幕骤然亮起,开始播放同性恋人亲密相拥丶亲吻的画面。
那画面明明是他藏在心底的温柔,此刻却像淬了毒的针,刺得他眼睛发疼。紧接着,电流“嗡”一声钻透皮肤,瞬间窜遍全身。
刹那间,姜野感觉有千万根烧红的针猛地扎进身体,疼得他浑身痉挛。
电流在太阳xue里横冲直撞,头疼欲裂,像是脑壳正被人用锤子强行撬开,脑浆都要跟着晃出来。
腹部剧烈地痉挛抽搐,五脏六腑都像被搅在了一起,恶心感直冲喉咙,却吐不出任何东西。
他本能地挣扎,皮带深深勒进肉里,手腕与脚踝很快勒出一道道红痕,渗出血丝也浑然不觉。
他想喊,想骂,声音却被痛苦死死吞噬在喉咙里,唯有破碎的呜咽声断断续续挤出喉咙,嘶哑得不像人声。
短短一分钟,漫长得像过了一生。
姜野的视线早就模糊了,屏幕上的画面和浑身的剧痛缠在一起,搅得他意识混乱。
恍惚间,他忆起晚自习後,在学校後街的路灯下,他偷偷牵起沈宁的手。
那时沈宁的指尖微凉,被他攥在掌心捂了会儿就暖了,两人的指缝相贴,带着少年人纯粹的欢喜,何等美好。
可如今,这份美好却被硬生生化作钻心的剧痛,逼他去厌恶丶去否认。
他死死咬着牙,牙龈都咬出了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忘,不能厌,这不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