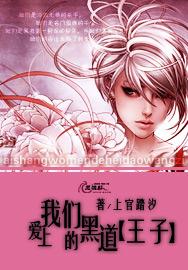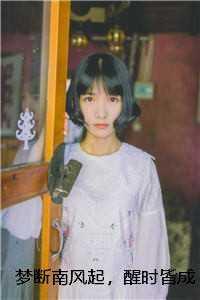紫夜小说>德云语录爱情 > 第94章 张九驰&夏之桐(第1页)
第94章 张九驰&夏之桐(第1页)
那天午后,空气凝滞得如同一块滚烫的、半透明的琥珀。窗外老槐树纹丝不动,叶片被晒得蔫蔫地卷着边,蝉鸣声嘶力竭,像是无数把生锈的小锯子,在夏之桐的耳膜上反复拉扯。教室里吊扇徒劳地嗡嗡旋转,搅起的只有阵阵烘热沉闷的气流,带着粉笔灰和汗水的味道,扑在脸上,黏腻得让人喘不过气。
夏之桐坐在靠窗的位置,眼皮沉得像是坠了铅块。摊在面前的数学练习册上,那些原本就面目可憎的几何图形,此刻更是扭动着、模糊成一片混沌的墨色。钢笔尖悬在纸上,墨迹凝聚成一颗越来越大的黑痣。笔尖终于落下,在空白处洇开一个微小的墨点,随即晕染开一小片模糊的灰色,像她此刻困倦而混沌的思绪。意识像浸了水的宣纸,一点点被睡意渗透、软化,最终彻底沉没。她脑袋一歪,额头轻轻抵在了微凉的手臂上,手中的钢笔却并未完全脱力,松松地夹在指间。
就在意识彻底滑入深眠的边缘,某种奇异的感觉猛地攫住了她。那感觉并非来自外界,而是从她握笔的右手内部骤然爆——一股冰冷、坚硬、带着不容置疑指令意味的力量,如同一条钢铁的神经瞬间注入了她的血肉!她的右臂猛地绷紧,像被无形的线提拽着,完全脱离了她昏沉大脑的掌控。
钢笔尖重重戳在纸上,出“嚓”的一声轻响。冰凉的金属笔杆硌着她的指节,墨汁顺着笔尖的缝隙涌出,在粗糙的作业纸上留下一个突兀、丑陋的墨团。紧接着,那失控的力量牵引着她的手腕,以一种僵硬却极其快的姿态,在纸上划动起来。笔尖刮擦纸面,出沙沙的锐响,刺耳得令人牙酸。
“张——”一个扭曲的、笔画粘连的字迹出现在墨团旁边,每一笔都带着一种被强迫的、生拉硬拽的狠劲。
夏之桐一个激灵,像是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瞬间从昏睡中惊醒!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狂跳,撞得肋骨生疼。她猛地抬起头,瞳孔因为惊骇而急剧收缩。右手!她的右手!那只握笔的手,此刻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冰冷铁钳牢牢夹住,仍在疯狂地动作!她甚至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手指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出的轻微“咔”声,那支廉价的塑料笔杆仿佛随时会被捏碎。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直冲头顶,头皮阵阵麻。
“不!”她喉咙里挤出短促的、带着哭腔的惊叫,本能地使劲甩动右臂,身体因为对抗那股巨大的力量而微微颤抖。但那只手仿佛已不再属于她,它顽固地、机械地继续着书写。
“九——”笔尖在纸上拖曳,竖钩拉得又长又直,如同划下一道冷酷的伤痕。
恐惧像冰冷的藤蔓瞬间缠紧了她全身。她使出吃奶的力气,左手也下意识地死死抓住自己失控的右腕,试图将它扳开、按停。然而一切都是徒劳。那股力量蛮横无比,她的抵抗如同蚍蜉撼树。笔尖毫无滞涩,流畅地、甚至带着一种诡异的韵律,落下了最后一笔。
“驰。”
“张九驰”。
三个字,以一种近乎痉挛的、力透纸背的姿态,歪歪扭扭又异常清晰地烙印在数学练习册的空白处,就在那个丑陋的墨团旁边。笔画生硬,转折处带着毛刺,墨色浓郁得乌,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又像是某种绝望的呼喊凝固在了纸上。
那股冰冷的、控制着她的力量倏然抽离。右手骤然一松,沉重的钢笔“啪嗒”一声掉落在练习册上,滚了几滚,在纸面上留下一道断断续续的墨痕。夏之桐像被抽掉了骨头,整个人瘫软在椅子里,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冰凉地贴在椅背上。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胸口剧烈起伏,心脏在耳边咚咚狂响,盖过了窗外依旧喧嚣的蝉鸣。她死死盯着那三个墨迹未干的字,眼神里充满了极度的茫然和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
“张九驰”?这是谁?她从未听过这个名字。刚才……那是什么?鬼压床?还是某种她无法理解的、来自身体内部的可怕痉挛?
夏之桐猛地合上练习册,仿佛那三个字是某种会咬人的活物。她把册子紧紧抱在胸前,像是抱着一个滚烫的秘密。接下来的课,老师的讲解变成了一片模糊的背景噪音,那些字句在她耳边盘旋,却无法进入她的脑海。她的指尖冰凉,目光不受控制地一次又一次扫过桌面上那本紧紧合拢的册子,每一次触碰那硬邦邦的封面,都仿佛能感受到从纸页深处透出的那股冰冷的、诡异的力量残余。
放学铃声一响,她几乎是第一个冲出了蒸笼般的教室。傍晚的空气依旧燥热,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和同学结伴,而是低着头,脚步匆匆,几乎是跑着回到了家。木质楼梯在她脚下出急促而空洞的呻吟。
“砰”的一声关上自己小房间的门,隔绝了楼下厨房传来的锅铲碰撞声,她才靠着门板,长长地、颤抖地呼出一口气。房间里残留着午后的闷热。她走到书桌前,几乎是带着一种仪式感般的郑重和恐惧,再次翻开了那本数学练习册。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张九驰”。
三个字静静地躺在那里,墨迹已干,显得更加突兀和刺眼。她伸出手指,小心翼翼地、用指尖最轻的部分,碰了碰那三个字。纸面冰凉光滑,除了墨水的触感,再无其他。没有预想中的灼热或者刺痛,也没有任何自然的感应。但这普通的触感,反而让她心头那股寒意更深了。
必须弄清楚!一个念头异常清晰地冒了出来。她拉开书桌抽屉,里面堆放着初中以来所有的同学录。花花绿绿的封面,贴满了大头贴,写满了各种祝福和略显稚气的签名。她一本一本地翻找,动作又快又急,纸张哗哗作响。她的目光像扫描仪一样,飞掠过每一页的名字栏。小学的、初一的、初二的……没有。同年级其他班的?她甚至翻出了几张初入校时填写的兴趣小组报名表,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单里,也丝毫没有“张九驰”的踪迹。抽屉被她翻得一片狼藉,可那个名字,如同沉入大海的石子,毫无踪影。
第二天课间,她拉住平日里消息最灵通、号称“年级小广播”的班长李悦,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丝自己都未察觉的紧张:“哎,李悦,你听说过……一个叫‘张九驰’的人吗?我们年级的,或者……以前毕业的学长学姐?”
李悦正对着小镜子整理刘海,闻言愣了一下,歪着头想了想,镜片后的眼睛眨了眨:“张九驰?没印象啊。这名字挺特别,要是有,我应该记得。”她看着夏之桐有些白的脸色,好奇地追问,“谁啊?找他有事?”
“没……没什么事,”夏之桐连忙摇头,掩饰性地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就……就随便问问,好像听谁提过一嘴。”她匆匆结束了对话,转身离开。身后传来李悦和其他女生低低的议论和轻笑声,像细小的针,扎在她紧绷的神经上。
她又去问了几个平时关系还不错的同学,甚至鼓起勇气问了隔壁班的班主任老师。得到的答案都是清一色的摇头和茫然的眼神。这个名字,仿佛只存在于她那张被墨汁污染的练习册上,一个孤零零的、无人认领的幽灵。
寻找的线索像断掉的风筝线,让夏之桐陷入更深的迷雾。那个名字像一枚冰冷的钉子,楔入她的日常,带着挥之不去的寒意和隐秘的重量。她开始下意识地在各种场合寻找线索——路过学校的布告栏,目光会不由自主地扫过那些褪色的表彰名单或活动通知;翻看借阅的旧书,会格外留意扉页上可能留下的借阅者签名;甚至连父亲随手放在茶几上的旧报纸,她也会趁他不注意时,飞快地浏览上面的寻人启事或者本地新闻栏目。每一次徒劳的搜寻,都让“张九驰”这三个字在她心里烙得更深,也更显得诡异。
周末的午后,窗外蝉鸣依旧不知疲倦。父亲夏明远难得没有去学校加班,坐在客厅的旧藤椅上,戴着老花镜,正专注地翻阅一本厚重的、纸张泛黄脆的册子。那是他耗费多年心血收集整理的本地地方志资料,里面记载着这个城市,特别是他们居住的这片老街区近百年的变迁。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特有的、带着微尘的干燥气味。
夏之桐给父亲端了杯茶,目光扫过他膝头摊开的书页。泛黄的纸上印着密密麻麻的繁体字和模糊的黑白照片。她犹豫了一下,心脏在胸腔里不规律地跳动着,最终还是走了过去,挨着藤椅扶手坐下。
“爸,”她的声音有点干涩,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藤椅粗糙的边缘,“那个……你知不知道,以前我们这条巷子里,或者附近,有没有一户姓张的人家?”
夏明远从泛黄的书页上抬起头,推了推滑到鼻梁上的老花镜,有些意外地看着女儿:“姓张?这条巷子里以前住的人家可不少,姓张的……也有几家吧。怎么突然问这个?”
夏之桐的心猛地一紧,她舔了舔有些干的嘴唇,那个名字几乎要脱口而出,却又被一股莫名的恐惧压了下去。她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是纯粹的好奇:“没什么……就是最近对老街的历史有点兴趣。那……有没有一个叫……”她顿了顿,声音不由自主地放得更轻,“叫张九驰的人?”
“张九驰?”夏明远重复了一遍,眉头微微蹙起,似乎在记忆的尘埃里努力翻找。他摘下老花镜,用指腹揉了揉眉心。客厅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单调的蝉鸣和老座钟缓慢的滴答声。夏之桐屏住了呼吸,感觉时间被拉得很长很长。
“张九驰……”夏明远喃喃道,眼神有些放空,像是穿透了眼前的墙壁,望向遥远的过去。过了好一会儿,他像是想起了什么,眼神微微一亮,带着一种追忆往事的感慨,“哦!你说的是那个孩子啊!想起来了!”
夏之桐的心跳骤然漏了一拍,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倾了倾,急切地问:“谁?爸,他是谁?”
“唉,”夏明远叹了口气,重新戴上眼镜,手指轻轻点着摊开的地方志上某张模糊的街道老照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都是小时候听你爷爷零碎提起的。抗战那会儿,兵荒马乱的……大概四十年代初?我们隔壁院子,住着一户姓张的人家,是从外地逃难过来的。他家有个半大小子,好像……就叫张九驰。”他的声音低沉下来,带着历史的沉重感,“那孩子,年纪不大,听说挺聪明的,就是命不好。后来……重庆大轰炸,老惨了,多少房子都炸没了,多少人……唉,那孩子,好像就是在那时候没了的。你爷爷后来还念叨过,说多可惜的一个娃……”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没了?”夏之桐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在……在轰炸里?”
“是啊,”夏明远点点头,脸上带着唏嘘,“那场大轰炸,毁了多少家啊。张家好像就剩了个小女儿被亲戚接走了,后来也再没音讯。唉,都是过去的事了。”他重新低下头,目光落回那些承载着沉重记忆的文字上,似乎陷入了沉思,不再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