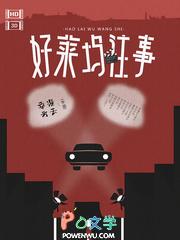紫夜小说>德云语录爱情 > 第99章 郑九莲&许言凝(第1页)
第99章 郑九莲&许言凝(第1页)
江南的梅雨,黏腻又执着,仿佛天空永无止境的泪痕,在慈安医院灰白色的高墙上蜿蜒流淌。陈默站在住院部楼下,仰头望着七楼那扇紧闭的窗。空气里浮沉着消毒水的锐利气味,混合着湿土和植物腐败的隐约气息,沉甸甸地压着人的肺腑。他肩上的相机包带子勒得肩膀生疼,心里却揣着个滚烫的念头——去捕捉一个被传颂为“人间至情”的故事:郑九莲与许言凝。
推开o病房的门,一种被生活反复捶打后特有的气味扑面而来。药味、消毒水的冷冽、某种身体衰败带来的难以言喻的气息,还有一丝微弱却倔强的花香——窗台的小瓶里插着几枝半蔫的白色雏菊。郑九莲靠在摇起的病床上,瘦得惊人,薄薄的被子下几乎显不出身体的轮廓。许言凝就坐在床边的矮凳上,背对着门,正用一把小勺,极其专注地搅动着碗里热气腾腾的粥。她的背影单薄,肩胛骨在洗得旧的米色开衫下微微凸起。
“郑先生,许小姐?”陈默的声音放得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许言凝闻声回头。那张脸带着明显的疲惫,眼下的青影很重,嘴唇也有些干裂,可那双眼睛望过来时,却像被雨水洗过的天空,清澈又沉静。她对他微微颔,嘴角牵起一个极淡的弧度:“陈记者?请进。”
陈默说明来意,声音在寂静的病房里显得有些突兀。他捕捉到郑九莲的目光,那目光先是带着病人惯有的疏离和倦怠,在他身上停留片刻,又缓缓移开,落在许言凝身上。那眼神里的东西瞬间变了,像寒冰化开,涌动着温热的泉流。
“九莲,是报社的陈记者,想……看看我们。”许言凝的声音很柔和,带着抚慰的意味,她舀起一勺粥,仔细吹凉,才递到郑九莲唇边,“来,再吃点。”
郑九莲顺从地张嘴,吞咽的动作缓慢而费力。他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许言凝的脸,那里面盛满了全然的信赖和一种深不见底的眷恋。陈默心头一热,职业的本能让他悄悄退后一步,手指无声地搭上挂在胸前的相机包扣,指尖触到了冰凉的金属机身。
日子如窗外连绵的雨丝,无声滑过。陈默成了o病房的常客。他带着笔记本,更多时候只是安静地坐着,看,听,感受。他看见许言凝如何熟练地为郑九莲按摩水肿的小腿,手指力道恰到好处,避开那些因长期输液而青紫硬的血管;他听见深夜郑九莲因疼痛出的压抑呻吟,紧接着便是许言凝起身倒水、拿药、低声安抚的窸窣声响,那声音如同摇篮曲,固执地对抗着无边黑夜的啃噬;他看见郑九莲在又一次艰难的呕吐后,虚弱地靠在许言凝瘦弱的肩头喘息,许言凝则用温热的毛巾,一遍遍擦拭他额角的冷汗和嘴角的污渍,动作轻柔得像擦拭一件稀世瓷器。
“许小姐,真不容易。”护士小张趁着换药间隙,在走廊里对陈默轻声感慨,语气里满是敬意,“郑先生这情况……说实话,太熬人了。可许小姐,愣是一声不吭,没见她抱怨过一句,也没掉过一滴眼泪。白天黑夜守着,郑先生稍微好点,她就笑,郑先生难受,她就陪着熬……这份心啊,石头看了都得软。”
陈默默然点头,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病房里。许言凝正弯着腰,帮郑九莲调整枕头的位置,侧脸线条在午后昏蒙的光线里显得格外柔和坚韧。这病房如同风暴中的孤岛,她便是那唯一的锚,任凭惊涛骇浪,兀自岿然不动。她平静的面容下,是否也藏着惊涛骇浪?陈默无从得知,只感到一股沉甸甸的敬佩压在心口。他相机里那些偶然捕捉的瞬间——她疲惫时撑在床边的手,她望着窗外时瞬间失神的侧影,都成了这无声坚守最有力的注脚。
一个闷热的午后,空气凝滞得仿佛能拧出水来。郑九莲午睡时被一阵剧痛攫住,身体骤然蜷缩,喉咙里溢出痛苦的呜咽。陈默正坐在角落整理笔记,闻声惊起。只见许言凝已经扑到床边,一边焦急地按铃,一边试图安抚:“九莲,九莲,我在!忍一忍,医生马上来!”
郑九莲的额角瞬间布满冷汗,身体不受控制地痉挛,挣扎着要下床。许言凝毫不犹豫地用自己单薄的身体架住他沉重的臂膀,咬紧牙关,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支撑着他,一步一挪地往病房内狭小的卫生间移动。她的脸因用力而涨红,纤细的手臂绷紧如弓弦,脚下微微颤,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仿佛在拖拽一座沉重的大山。陈默想上前帮忙,却被许言凝一个异常坚定、甚至带着点凌厉的眼神制止了。那眼神无声地传递着一种属于他们的、不容外人介入的隐秘尊严。那一刻,陈默伸出的手僵在半空,一股混合着震撼与无力的激流猛地冲击着他。
郑九莲终于虚弱地躺回床上,疼痛的余波让他喘息不止。许言凝拧了热毛巾,细致地擦拭他汗湿的脖颈和脸颊。郑九莲闭着眼,嘴唇翕动,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阿凝……我是不是……太拖累你了……”他枯瘦的手指下意识地蜷缩着,抓住了被单的一角,指节因用力而白。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许言凝的手顿了一下,随即用毛巾轻轻拂过他紧蹙的眉心,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却又像绷紧的弦:“说什么傻话。我们不是说好的吗?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她的目光落在郑九莲因疼痛而扭曲的脸上,眼神深处翻涌着无法言说的痛楚,但语气却异常坚定,仿佛在对抗某种巨大的引力。陈默注意到她握着毛巾的手背,青筋微微凸起,指节同样因用力而泛白。
某天,陈默来得早些,许言凝正靠在窗边闭目养神。一本翻开的杂志滑落在她脚边的地上。陈默走近想帮忙拾起,目光不经意扫过摊开的页面——那赫然是一本精美的婚庆杂志,内页展示着洁白的婚纱和璀璨的钻戒,洋溢着与这间病房格格不入的幸福气息。陈默的手僵住了。就在这时,许言凝似有所觉地睁开眼,看到地上的杂志,脸上瞬间掠过一丝慌乱和无措,如同一个被窥破心事的少女。她飞快地弯腰捡起杂志,胡乱地塞进旁边的帆布包里,动作带着明显的狼狈。她没有看陈默,只是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帆布包的带子,耳根泛起不易察觉的红晕。那短暂的羞赧和狼狈,像一根尖锐的刺,猝不及防地扎进陈默心里,让他窥见了平静海面下那令人窒息的巨大冰山的一角。原来她心里从未停止过对未来的憧憬,哪怕那未来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病房里,郑九莲的精神难得地好了一些。窗外,久违的阳光穿透厚重的云层,吝啬地洒下几缕金辉,恰好落在靠窗的病床上,温柔地包裹着郑九莲枯槁的脸和许言凝低垂的颈项。许言凝正低声读着一本旧诗集,声音轻柔,像溪水流过卵石。郑九莲微微侧着头,专注地听着,浑浊的目光落在许言凝身上,带着一种近乎贪婪的眷恋。阳光给许言凝的丝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也将两人相依的身影柔和地投在洁白的墙壁上,构成一幅宁静而圣洁的剪影。这瞬间的美好如此脆弱,又如此珍贵,仿佛黑暗深渊里骤然绽放的一朵小花。
陈默的心被这画面击中了。他几乎是屏住呼吸,身体里那个记者的灵魂在呐喊:就是此刻!他悄无声息地、极其缓慢地举起胸前的相机。镜头,冰冷的金属镜头,小心翼翼地、贪婪地对准了那片被阳光和温情笼罩的方寸之地。取景框里,许言凝专注阅读的侧脸,郑九莲凝视她的目光,光影在他们周围流淌……一切都完美得如同精心设计的剧照。他的食指,带着职业的敏锐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轻轻搭在了冰凉的快门按钮上。
就在那千钧一的瞬间,郑九莲的头忽然动了一下。他的视线,不再是投向许言凝,而是穿透那温暖的阳光,精准地、直直地刺向陈默手中那个黑洞洞的镜头!那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重的疲惫和一种陈默无法理解的、近乎恳求的决绝。
一只枯瘦的手,带着惊人的度抬了起来。嶙峋的指骨,皮肤薄得几乎透明,清晰地映出下面青紫色的血管脉络。那手在空气中划过一个微弱却无比坚定的弧度,稳稳地挡在了镜头和许言凝之间,像一面骤然竖起的、脆弱不堪却又坚不可摧的盾牌。
陈默僵在原地,快门终究没能按下去。病房里只剩下许言凝低柔的诵读声和窗外模糊的车流声。
郑九莲的手依旧固执地挡在那里,微微颤抖着。他望着陈默,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极其缓慢地、极其艰难地,扯出一个温和的弧度。那笑容在他枯槁的脸上绽开,如同龟裂土地上绽放的花,带着一种令人心碎的平静。
“别拍。”他的声音很轻,像羽毛落地,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清晰地钻进陈默的耳朵里,也钻进了一旁许言凝骤然停止的诵读声中。
许言凝拿着书的手猛地一颤,书页“哗啦”一声轻响。她抬起头,目光从书本茫然地移到郑九莲脸上,又移到那只挡在镜头前、微微颤抖的手上。她的嘴唇瞬间失去了血色,微微张开,却不出任何声音,像一尊骤然被冻结的雕像。
郑九莲的目光掠过许言凝瞬间苍白的脸,最终又落回到陈默身上。那温和的笑容还在,只是眼底深处翻涌起无法言喻的痛楚和一种近乎残酷的清醒。他顿了顿,每一个字都像是耗尽了他仅存的生命力,清晰而缓慢地吐出:
“以后……她还要嫁人呢。”
“别拍,以后她还要嫁人呢。”
这十个字,如同十颗冰冷的子弹,接连射入病房凝滞的空气里。陈默举着相机的手臂像是被无形的电流击中,猛地一沉,相机差点脱手滑落。他本能地用手指死死扣住机身边缘,冰冷的金属棱角硌得掌心生疼。他脑子里一片轰鸣的空白,职业性的冷静外壳被这句话击得粉碎,只剩下一种赤裸裸的、被巨大悲悯淹没的茫然。原来那份平静的凝视里,早已容纳了比病痛更深、更沉重的考量——直至生命尽头,他仍固执地、笨拙地,试图为她挡去一切可能的风霜,哪怕只是一缕投向未来的、可能并不存在的目光。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他几乎是狼狈地垂下手臂,相机沉重的分量带着他微微踉跄了一下。快门按钮在仓促的下落中,被他的拇指边缘无意识地擦过。
“咔嚓——”
一声轻微却无比清晰的机械声响,突兀地刺破了病房里死一般的寂静。
许言凝像被这声音狠狠抽了一鞭子。她一直维持着的、如同精美瓷器般脆弱平静的面具,在这声轻响中瞬间碎裂。她猛地从矮凳上弹起来,动作快得带倒了凳子,出“哐当”一声刺耳的噪音。那本诗集从她骤然失力的手中滑脱,“啪”地一声掉在地上。她根本顾不上这些,整个身体绷紧如惊弓之鸟,那双总是平静地处理一切、温柔地拂过郑九莲病容的手,此刻却像秋风中的枯叶,无法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她的目光死死地、惊恐地盯在陈默垂下的相机上,仿佛那不是相机,而是对准她心脏的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