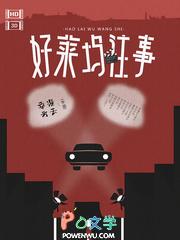紫夜小说>甄嬛传之安陵容绝色 > 第26章 憋闷安父再吃亏买侍女的银两到手(第1页)
第26章 憋闷安父再吃亏买侍女的银两到手(第1页)
安比槐是蹙着眉头,进入安陵容她们娘仨所在的偏院的。
眼睛里的嫌弃之情也是溢于言表。
而当他满脸不悦,站在娘仨不远处的时候,安陵容是正在按娘亲的描述,画着芙蓉花的花样子的。
萧姨娘则是在一旁观看,顺带称赞安陵容画画有天赋。
场面看着,是既和谐,又温馨。
不过看在安比槐的眼里,又是另一种感觉了
上午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他的那口憋屈气,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消,只是安陵容她们娘仨都表现得十分“正常”,让他找不到泄的出口而已。
而明明他都已经退步妥协了,娘仨居然还不赶紧搬过去,并且还一副和乐融融的样子。
所以在安比槐看来,不止很碍眼,还感觉是在挑衅他的家主威严!
“夫人,你们怎么还在这?!
不是让你们尽早搬过去吗,怎么东厢都收拾好了,你们却没个动静!
你们是又反悔了,觉得东厢房不好,想搬到正房去?
还是见不得老爷我好,想明天被白老大夫撞见,好将你们的情况宣扬出去,让老爷我被人戳脊梁骨啊?!”
安比槐还是一如既往的色厉内荏。
至少这副样子却很能将林秀吓唬得住。
林秀下意识地连忙起身想要辩解,只是说不出一句有效的辩言。
“老爷!不,不是,我们”
安陵容扫了一眼娘亲慌乱起身,被撞到的腿,眼里闪过一丝心疼和愠怒。
不过终究还是更心疼娘亲被安比槐逼问得心焦,慌神,不知所措,所以抢在萧姨娘冒头出言讽刺之前,将之前已经想好的“剧本”,冷静又夸张地演绎了出来——
“父亲!您误会我们了!
母亲满心满眼都是父亲,怎么会舍得让父亲为难,受一丁点儿的指责!
这院子我们都安心住了几年了,东厢房比起这院子不知好了多少,又怎会不满足!
至于‘想让父亲被人戳脊梁骨’这样的话,这更是在戳母亲的心啊!”
安陵容带着些许哭腔,“焦急”又“委屈”地大声向安比槐申诉,把蒙冤受屈之态做足。
安比槐看了一眼安陵容,又看了一眼浑身散着自内心的委屈和眷恋的林秀,总算相信了几分。
气势缓和了下来,又叹了一口气,“好吧,那是什么原因,让你们不愿搬过去呢?”
安陵容趁热打铁。
“父亲,非是我们不愿,实是我们不能啊!
时间仓促,我们人手又少。
就我和母亲,姨娘三个,母亲的眼睛又
所以我和姨娘光是收拾整理这些零七碎八的家当,就收拾到了晚饭前。
可如果不用晚饭,怕是也不够力气来搬。
所以等做好晚饭,吃罢晚饭,再收拾善后,这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
父亲又难得休沐一天,我们若是漏夜慢慢搬抬过去,还指不定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弄完。
要是不小心出声响,影响父亲休息,这让我们又如何心安!
哎,这不,只想着明天早点过去,再在正房多待一点时间应付过去。
要是白老大夫问起,就是实话实说,他也不能说是父亲之过。”
安比槐听到这,就意识到了不对。
虽说安陵容话里全程没有指责他,不给她们安排帮忙搬东西的仆人,但是白老大夫不会听不出来这其中的问题啊!
所以他正准备委婉地提醒安陵容要补全这个漏洞,就听安陵容叹了一口气,颇为感慨地继续说道。
“哎,早知道,容儿就厚着脸皮,接受婷玉姐姐的馈赠了,那样好歹能多两个人手来帮忙”
安比槐立刻意识到了什么,顾不得安陵容之前话里的疏漏,眼神微眯,语气焦急地追问。
“什么意思?!”
安陵容立刻做出一副懵懂无知,被吓到了的样子,躲到林秀的身后,“怯怯”地回复。
“就,就第一次在茶楼见面的时候,全姐姐就曾好奇地问过,既然容儿是县丞之女,为什么我的身边没有随侍的丫鬟。
后,后来被容儿以‘求诊是私密之事,姨娘跟着稳妥些’给应对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