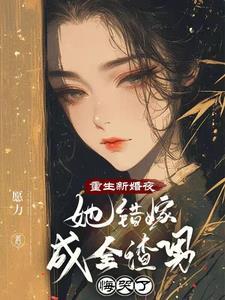紫夜小说>三国金手指是看广告宋公子晏 > 第85章 85 双标狗(第2页)
第85章 85 双标狗(第2页)
属下立刻回禀:“主公,源头已经很难追溯,但最先公开议论此事,并且言辞激烈的,是颍川本地的一些士族名士。特别是陈氏丶荀氏丶钟氏这几家,府中门客和依附他们的中小士族,都在推波助澜。”
谢乔冷笑,低声道:“果然如此。”
她明白,梁国旧势力的反扑是必然的,但颍川士族的反应,让她嗅到了一丝不同的味道。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风评被害”,背後恐怕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博弈。
谢乔心中透亮。颍川士族是想借此机会,敲打她,维护他们的清流地位,顺便打压她这个不按规矩出牌的异类。
她太清楚颍川士族在中原地区乃至整个大汉天下的特殊地位了。
东汉重经学,而颍川,正是经学传承的核心地带。
这里的几大世家,如荀氏丶陈氏丶钟氏丶韩氏等,以家族为核心,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代代研习和阐释,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家学体系。
颍川士族不仅垄断了经学的解释权,更凭借这种学术优势,源源不断地向朝廷输送人才,占据太学博士丶郡国守相丶朝中公卿等显要职位。
东汉奉行“以经取士”的制度,使得颍川士族牢牢把控了人才选拔的话语权。
他们更是通过遍布朝野的门生故吏,结成了一个庞大而稳固的政治学术同盟。
而其他地域的学者,尤其是寒门出身者,想要突破这层壁垒,进入权力的核心圈,难如登天。
这也是为什麽谢乔能在梁国相对容易地招揽到一批有才华却郁郁不得志的人,因为在正常的轨道上,他们很难与颍川士族子弟竞争,难以被朝廷着意。
更有,颍川士族还掌握着“清议”这件武器。
所谓“清议”,一种由士大夫阶层主导的舆论活动,包括南阳汝南一带盛行的“月旦评”,本质上都是士人阶层用以臧否人物丶褒贬时政的舆论工具。
在太平年月,这种评议或许还能对官员品行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在东汉末年这等讲究门第出身丶人情关系盘根错节的时代,它早已变了味。
颍川士族以德行着称,通过自身操守赢得社会声望,通过品评人物丶臧否时政丶标榜道德,成功塑造了自身“清流”领袖的文化权威形象。
而党锢之祸中,他们又与太学生联合,抨击宦官集团,导致在“党锢之祸”中被镇压,这反而强化了其“正义代言人”的地位。
谁若是被他们打上了负面标签,往往声名狼藉,寸步难行。
一言可以扬名,一语亦可灭人。
现在,她在梁国大刀阔斧改制,重用非颍川籍丶甚至寒门出身的人才,打破了他们潜在的人才垄断格局,又行事不循传统士族规矩,自然就成了他们眼中需要打压的“异类”。
梁国旧势力的怨恨,恰好为他们提供了攻击的口实和民意基础。
谢乔如今就面临着被“清议”审判的危机。
她很清楚,颍川士族的影响力非同小可,任由这股负面舆论发酵,後果不堪设想。
以讹传讹,人言可畏。
谣言不及时止住,不仅会严重影响她在颍川乃至整个士林中的声誉,影响招揽英才的大计,更可能被扣上难以洗刷的政治污点,为她未来的发展,埋下巨大隐患。
谁愿意投奔一个声名狼藉的主君?
谢乔眼神逐渐变得锐利起来。
这些个造谣诽谤者,让她莫名想起原世界里,在她剪的视频里满嘴喷粪的小黑子。
应对小黑子,她可以拉黑举报无视,这里却不能。
“谢府君,”国丞周密忧心道,“斥候传回消息,颍川那边,言辞颇为激烈,已有多家名士公然表示对府君行事不满。”
谢乔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远处的天空,心中做出了决定。
必须去趟颍川,亲自解决这件事。
颍川,士族盘踞之地,人言如同,如同龙潭虎xue,此行必然凶险。
但谢乔知道,她避无可避。
想要彻底扭转风评,掌控舆论,就必须直面风暴的中心。
“控评”,这一现代网络用语,此刻却无比精准地概括了谢乔的目的。
她要去颍川控评,为自己正名,为梁国未来的发展扫清障碍。这盆脏水,必须想办法挡回去,甚至泼回去!
决心已下,谢乔开始考虑随行人员。
硬碰硬肯定不行,得有策略。她思忖片刻,点了一个名字:“传令,召毛玠前来。”
毛玠,字孝先,陈留平丘人,虽非颍川核心士族,但也尝游学颍川。其人处事稳重,熟悉经义,在之前的实习中表现突出,已被任命为县丞,能力卓越。带上他,既能作为熟悉当地情况和经学辩论的助手,也向外界展示梁国唯才是举并非虚言。
对外,就宣称是前往颍川考察风土人情,学习先进经验。
另外,从西凉铁骑中挑选一百精锐,秘密随行,在外围接应,以应对最坏情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