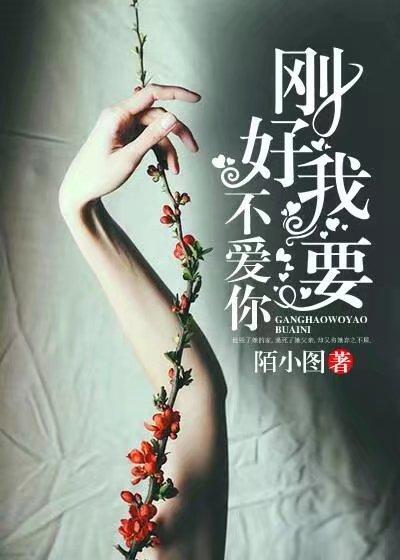紫夜小说>三国金手指是看广告宋公子晏 > 第95章 95 老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第2页)
第95章 95 老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第2页)
哪里是什麽“人傻钱多”,分明是眼光独到的活财神!
当初那笔入股的钱,不仅救活了她这濒死的店,现在更是让她赚了个盆满钵满。
她悄悄盘算着,照这势头下去,到年底分红时,可得给那位乔先生封一个厚厚的大利是。不,光有利是还不够,得再备上一份体面的谢礼才行,这知遇之恩,可不能忘了。
她一边想,一边又扯着嗓子吆喝起来:“小二!赶紧的,楼上李先生的洗脚水!”
福安客栈那样的店家绝非个例。
街面上人流明显多了起来,摩肩接踵,不少生面孔操着外地口音,四处打听着官学和梁园的方向。
茶楼里,原先说书先生讲的什麽才子佳人丶江湖恩怨,如今十有八九都换成了圣人轶事,什麽“桥茂跪拜”丶“王良顿悟”,还有各种新编的圣人显灵段子,听得茶客们津津有味,赏钱给得格外大方。
跑堂的夥计脚下生风,添水都快忙不过来。
酒肆之中,更是热闹非凡。那些滞留在此丶日日去官学碰运气的文人墨客们,似乎找到了新的消遣。他们不再只是唉声叹气,反而三五成群,围桌而坐,就着几碟茴香豆,一壶浊酒,高谈阔论。讨论的焦点也彻底从风花雪月丶诗词歌赋,转向了谁的问题更有深度,谁的见解更近圣人之意。往往为了一句经文的注解,争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声音能传出几条街去。有时争到酣处,还会当场铺开纸笔,引经据典,互相辩驳,仿佛自己才是得了圣人真传的那个。这些人一坐就是大半天,酒水菜肴消耗得飞快,账房的算盘珠子都快磨平了。
谢乔对此乐见其成。
她当初入股这些店铺,未尝没有借圣人东风,刺激梁国经济,顺便给自己回笼资金的考量。
如今看来,效果显着。
王都之外,则是另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
那一万八千名黄巾俘虏,在经历了最初的惶恐丶绝望与麻木後,渐渐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找到了某种平静。
有饭吃,管饱,虽然滋味谈不上好,但比起过去吃了上顿愁下顿,甚至啃树皮嚼草根的日子,强了不知多少倍。
身上穿着统一发放的粗布衣,虽然简陋,却也能遮风御寒。
干活是累,每天收工时骨头像散了架,可夜里能安稳睡在临时搭建却也挡风的棚屋里,不必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官兵或乱匪。
最重要的是,做满三年丶恢复民籍,按人头发放钱粮的承诺,像一盏昏黄却实在的油灯,照亮了他们的前路。
这盼头太具体了,具体到可以数着日子过。
三年,一千多个日夜,咬咬牙,似乎也不是那麽遥不可及。
比起渠帅管亥许诺的那个虚无缥缈的太平盛世,这个承诺显得格外实在。
号子声在旷野上此起彼伏,俘虏们被编成百人为一队,在手持长矛的军士不远不近的看管下,挥舞着官府统一发放的铁锹和镐头。
汗水浸透衣背,在阳光下闪着光。坚硬的土地被一下下砸开丶撬松丶再被奋力挖起,堆到一旁。
一条条笔直的沟渠被挖出,又被填入碎石和夯土,路基的雏形在荒野上向前延伸。
这是在修建通往各处乡里的驰道,是谢乔规划中梁国交通网络的第一步。
要想富,先修路,此亘古不变之真理。
梁国地处中原腹地,地理位置优越,四通八达是优势,但也意味着无险可守。
发达的交通网能极大地促进内部物资流通丶人员往来,刺激经济,但同样也能让敌人长驱直入,兵临城下。
另一部分俘虏则在山中采石,在河边挖沙,在林间伐木。大量的石料丶木料和河沙被源源不断地运往睢阳城郊。
这些都是升级城防所需的材料。
伴随着一阵只有她能看见的光芒闪烁,系统开始自动作业。
原本的城墙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包裹,砖石挪移,结构重组。肉眼可见的,城墙的高度在增加,厚度在变扎实,墙体表面也变得更加光滑坚固,其上甚至多出了许多用于防御的垛口和射击孔。
谢乔伸手触摸着身前的墙垛。触手冰凉坚硬,质感致密得惊人,灰白色的墙体表面异常平滑,几乎看不出砖石拼接的痕迹,仿佛整段城墙连同新增的防御工事都是一次性浇筑而成,浑然一体,透着一股超越这个时代工艺的坚固气息。
目光所及,原本的三级土石城墙已然脱胎换骨。墙体拔高到了五丈,厚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三丈,巍峨耸立,予人坚不可摧之感。
城墙之上,结构复杂丶射孔密布的箭楼拔地而起,与城墙连接处严丝合缝。城门外侧,加筑了半月形的瓮城,将城门牢牢护在其中,形成了双重防御。更高处的了望台视野开阔,可以监控远方的动静。就连城门处的吊桥也变得更加厚重,绞盘机关隐于其後,显得精密而可靠。
谢乔估算着,若是没有系统,单凭人力,要将睢阳城墙修筑到如此规模和强度,动用数万劳力,日夜赶工,恐怕没有足年之功绝无可能。黄巾俘虏搬运来的石料丶木料丶河沙,在系统的伟力下,转瞬间便化作了眼前的钢铁堡垒。
看着焕然一新的城墙,谢乔心里踏实了不少。
在冷兵器时代,坚固的城防是抵御外敌最有效的屏障。梁国境内一马平川,一旦有变,这座四级城墙,将是梁国百姓的依仗。
这一年来,在她的治下,梁国无论是内部经济丶民生,还是外部防御,都在稳步提升,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梁国的安宁,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
据梁国周边哨卫传来的消息,局势并不乐观。周边州郡,诸侯之间的摩擦日益增多,小规模的冲突时有发生。
朝廷的诏令,早已出不了雒阳。
各地拥兵自重者,蠢蠢欲动。
平静的湖面下,暗流正在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