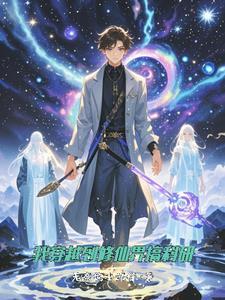紫夜小说>金戈什么作用 > 第42章 白马之盟定非刘不王(第2页)
第42章 白马之盟定非刘不王(第2页)
白马之盟后,朝堂格局生剧变。功臣集团彻底失去了封王的可能,虽仍有列侯爵位,却被严格限制兵权与封地灵脉资源。樊哙虽因祖巫血脉和皇亲身份(其妻吕媭是吕后之妹)得以保全,却主动上交了部分兵权,只求自保;陈平、周勃等人则谨言慎行,将重心转向行政事务,不敢再触碰军权。
“韩信、彭越的结局就在眼前,谁敢再提‘封王’二字?”群臣私下议论,对刘邦的猜忌心更加忌惮。有位曾随刘邦起兵的老将,只因酒后说“若论功,我也该封王”,便被削去爵位,贬为庶人,可见盟誓的威慑力。这种恐惧虽暂时稳定了朝堂,却也削弱了汉军的战力——功臣老将不敢放手施为,年轻将领又缺乏历练。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与此相对,宗室诸王的地位空前提升。刘邦为同姓王配备了精锐的“宗正军”,允许他们在封地内开采灵脉、训练修士,甚至拥有“灵犀弓”“玄铁甲”等重器。齐王府的谋士建议:“大王可借灵脉资源招揽炼气士,修炼‘齐地八阵’,将来若长安有变,可率军勤王。”这种建议虽看似忠诚,却暗含分裂的隐患——宗室权力过大,同样可能威胁中央。
吕后的外戚势力则采取了更隐蔽的方式扩张。她以“辅佐太子”为名,将吕家子弟安插在郎中令、卫尉等关键岗位,掌控宫城守卫;又通过李信等炼气士,暗中影响长安灵脉的分配,将“太乙灵泉”“骊山玉矿”等优质资源划归外戚掌控的工坊,积累实力。面对这种局面,刘邦并非毫无察觉,却因病重力不从心,只能偶尔敲打:“吕家子弟当安分守己,勿要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最尴尬的是萧何、张良等“中间派”。萧何既要执行刘邦的盟誓,又要平衡吕后的压力,整日如履薄冰;张良则干脆称病闭门,潜心研究《奇门遁甲》,对外宣称“不问政事”,实则在暗中观察局势,为太子刘盈积蓄力量。朝堂的分裂与猜忌,在白马之盟的光环下悄然加剧。
边境暗流:匈奴的威胁与盟誓的局限
白马之盟的庄严尚未散去,边境的急报便接连传入长安。匈奴冒顿单于统一草原后,实力大增,在“狼居胥山”现上古灵脉,修炼《山海经》记载的“噬灵功”,麾下骑兵吸纳灵脉之力,战力陡增。他们频频南下,袭扰代郡、云中一带,甚至与投降匈奴的韩王信暗中联络,企图里应外合。
“韩王信在太原囤积粮草,与匈奴使者往来密切,恐有反意。”陈平将密报呈给刘邦,“边境炼气士探查,匈奴营地的‘狼灵阵’已布设完成,骑兵数量不下四十万。”刘邦猛地坐起,咳嗽加剧:“韩王信乃朕所封,竟敢通敌?传朕令,命樊哙率军北上,先平韩王信,再拒匈奴!”
然而,此时的汉军已不复当年之勇。韩信等名将被诛,功臣老将畏缩不前,宗室诸王年幼无法领兵,只能由樊哙、周勃等老将勉强支撑。樊哙虽有祖巫血脉,勇猛有余却谋略不足;周勃擅长防御却不擅进攻,汉军的调度显得捉襟见肘。
刘邦看着边境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匈奴骑兵标记,第一次意识到白马之盟的局限——它能巩固内部皇权,却无法抵御外部威胁。“若韩信还在,何惧匈奴?”他喃喃自语,眼中闪过一丝悔意。但盟誓已立,功臣已诛,他只能硬着头皮推进:“朕要亲征!朕要让匈奴知道,刘氏江山不是好惹的!”
这个决定遭到群臣反对。萧何劝谏:“陛下龙体欠安,亲征风险太大,不如派宗室诸王率军前往。”吕后也假意劝阻,实则暗中希望刘邦离京,以便进一步掌控朝政。但刘邦心意已决:“朕身为天子,岂能坐视匈奴欺辱?朕要让天下看看,刘氏江山的守护者,不仅有盟约,更有刀剑!”
亲征的筹备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三十二万大军从关中、关东各地集结,萧何负责粮草补给,调用了长安附近所有的灵脉资源;李信率领炼气士随军出征,携带“破阵符”“镇煞旗”等法器,准备对抗匈奴的狼灵阵;宗室诸王中最年长的齐王刘肥,被命率军侧翼接应,这也是同姓王次参与大规模军事行动。
隐患深种:盟誓的裂痕与未来的阴影
刘邦亲征前,再次来到灵犀殿,望着被龙气封印的人皇玉玺,心中百感交集。他知道自己此行凶险,特意召来太子刘盈,指着玉玺道:“这是刘氏江山的根本,你要守住它,守住盟约,莫让外姓觊觎。”刘盈懦弱,唯唯诺诺,吕后在旁接口:“陛下放心,臣妾定会辅佐太子,死守盟约。”刘邦看着吕后,眼神复杂,最终只是叹了口气。
盟誓的裂痕在此时已悄然显现。“非刘氏不王”的誓言,将权力牢牢锁在刘氏手中,却也让朝堂失去了制衡外戚的力量——功臣集团凋零,宗室年幼,唯一能填补权力真空的只有外戚。而“祖巫血脉继承者可触玉玺”的规定,更是为吕后提供了可乘之机——她早已开始寻找“身怀祖巫血脉”的吕家子弟,为将来干预朝政制造“天命”依据。
长安的灵脉也因盟誓和即将到来的亲征而变得紊乱。李信向刘邦禀报:“陛下,长安龙脉的龙气因玉玺封印而略显滞涩,若再大规模抽调灵脉资源供大军使用,恐引灵脉动荡。”刘邦却不以为意:“江山都快保不住了,何惜灵脉?”他不知道,龙脉的滞涩正是权力失衡的预兆,外戚的阴煞之气已开始侵蚀龙气。
群臣中有人察觉到了危机。张良在给刘邦的密信中写道:“盟誓固权,却失人心;封王固宗,却养骄奢;血脉定玺,却留隐患。陛下亲征在外,当防内患甚于外忧。”但此时的刘邦已无暇顾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匈奴身上。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出前夜,刘邦在长乐宫设宴,与群臣告别。席间,他举起酒杯,望着殿外的星空:“朕起于沛丰,斩蛇起义,灭秦破楚,定鼎长安,靠的不是盟约,是人心。今日白马为盟,非不信群臣,是怕朕百年之后,有人忘了这江山是谁的。”他一饮而尽,眼中闪过一丝疲惫,“待朕破了匈奴,便归乡养老,与父老痛饮三日。”
然而,他终究没能实现这个愿望。亲征的大军在秋雨中离开长安,刘邦坐在车中,回望长乐宫的宫墙,隐约看到灵犀殿的方向闪过一丝异样的红光——那是外戚势力暗中滋长的阴煞之气,也是白马之盟埋下的第一颗隐患种子。他以为用鲜血和誓言筑起的屏障固若金汤,却不知人心的欲望与权力的博弈,从来都不是一纸盟约能约束的。
尾声:盟誓的余音与边尘的预警
白马之盟的余音在长安回荡,“非刘氏不王”的誓言成了悬在群臣头顶的利剑。宗室诸王在封地内开始积蓄力量,外戚在长安悄然扩张,功臣在谨慎中自保,朝堂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却又脆弱得不堪一击。
灵犀殿的玉玺依旧被龙气包裹,结界上的符文流转不息,仿佛在守护着刘氏的王权。但看守玉玺的侍卫中,已有吕后安插的亲信;负责监测灵脉的炼气士,开始向吕家传递龙脉动向;甚至连“祖巫血脉”的鉴定权,也渐渐落入外戚掌控的太常寺手中。
边境的战报越来越频繁。韩王信正式投降匈奴,引兵攻占太原,烧杀抢掠;冒顿单于亲率四十万骑兵南下,狼居胥灵脉的“噬灵功”让匈奴骑兵悍不畏死,汉军的前哨部队节节败退。樊哙率军抵达代郡,却因不熟悉匈奴战法和灵脉阵,战便失利,损失惨重。
刘邦在途中接到败报,急火攻心,咳嗽加重,却依旧强撑着下令:“加进军,朕要亲自会会冒顿小儿!”他不知道,这场亲征不仅将让他经历白登之围的耻辱,更将让长安的权力平衡彻底打破——他离京后,吕后以“监国”之名全面掌控朝政,白马之盟的裂痕,终将在匈奴的铁蹄与外戚的野心下,彻底撕裂。
长乐宫的梧桐叶落尽了,露出光秃秃的枝桠,像极了刘邦晚年的江山。白马饮血的痕迹早已干涸,但盟誓的誓言与隐患,却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伴随着汉室的兴衰,不断上演。而远方草原的风,正裹挟着匈奴的狼啸与灵脉的煞气,向着中原大地,步步逼近。
喜欢金戈玄秦请大家收藏:dududu金戈玄秦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