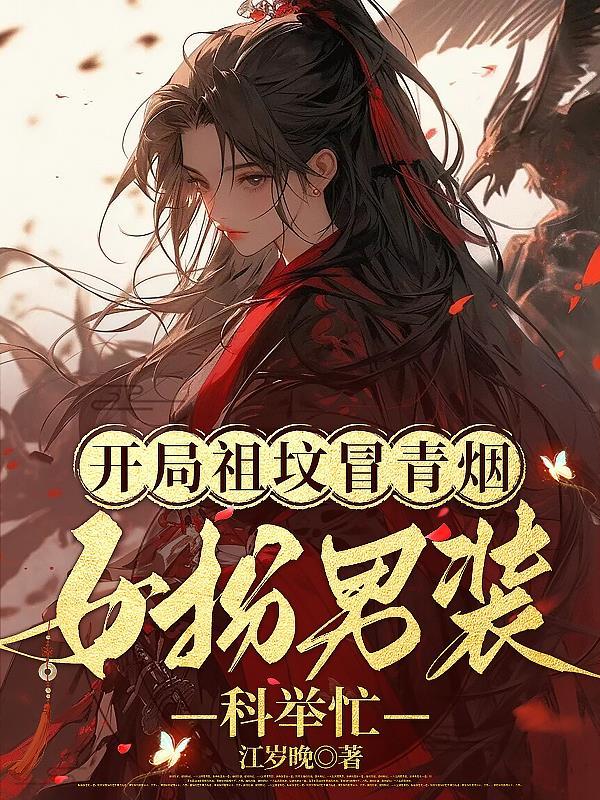紫夜小说>朕的一天番外 > 7080(第15页)
7080(第15页)
壶中茶将尽,她也从炕上起身。
第80章午时八刻又要走了吗?
赵有良如往常每一个在又日新外的早晨一样,向皇帝跪祝,“万岁爷吉祥。”
紧跟着东暖阁外伺候的人乌压压地一齐跪下去,声音回荡在风声里,让人无端生出些恍惚,竟不知眼前是梦,还是昨夜是梦。
连朝也跟着跪下去,双膝触地,柔软的栽绒地毯隔着棉袍贴近膝盖,口中重复的是与他们无异的话语。
“万岁爷吉祥。”
皇帝端坐炕上,神色难辨,听了这些年,头一回觉得,“吉祥”两个字从心尖上滚过,倒成了一种可笑的讽刺。
他也如往常一样,重复已经成为章程的话,“伊力。”
赵有良暗暗地觑了眼皇帝的神色,揣摩着说,“主子,已到寅正了。伺候盥洗梳头的人都在外头候着,您现在传进来么?”
皇帝只是看着她,“等一等。”
赵有良不知道这话,究竟是对谁说,只能先道,“嗻”,“奴才等在外头候着。”
东暖阁里又剩下他们两个。
外头天还没有亮,但是因为换了一遭灯,内外都更亮堂。
他知道天一亮,她就要离开。
他还是问出口,“又要走了吗?”
她微微怔忡,回答,“嗯。”
皇帝说,“好。我会备下灯和伞,让人送你到神武门。”
她再度俯首,“奴才谢主隆恩。”
赵有良在暖阁外轻轻地请,“万岁爷?”
皇帝答,“知道了。”
东暖阁的门边,设有一幅楹联。
不知道何时陈设的,至少在记忆里,先帝在时,它们就存在了。
也许更早,仁宗皇帝在时,它们已经挂在墙上。
他的祖父、父亲,都看过这两行字。
他御极三年,在养心殿起居的这么些时日,也许因为每日机务繁忙,竟从未认真地留意过。
此刻他看着她,也看见她身后不远处的两排字。
——无不可过去之事,有自然相知之人。
眼前事即是此事,眼前人即是此人。
她已经重新起身,却步要出去,他不知怎么,本能地忽然叫住她,“连朝。”
她回过头。
他凝望她良久,似乎总想好好地记住她。
也不知多久,最终只是很轻地说,“多谢你。”
他说,“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我种植的桑麻不断地生长,我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宽广。
总担心一场霜霰会随时来到,让它们轻易零落为野草。
后面的一些话,他未曾说出口,只是笃定她一定会懂得,也一定会知道。
——多谢你一直以来的坚持,为我保全了那么多我应该尽力去保全的人。
——多谢你一次又一次的警醒,让我不至于在无穷的权与欲中迷失。
让我重新认识,一个在天地间活着的人,应当是什么样子。
她这一次,回答以他曾经念给她听的诗,是在三希堂,少年天子虔诚地与她分享他的愿景,“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
她看向皇帝,虔诚祝祷,“您曾对我说过,年年桑麻有时,让天下人不必受冻馁离散之苦,是先帝一生的期待。时时有求新之心,永不懈怠,回馈生民,是您一生的期待。”
虽然期望与现实总有很多的差距,也许在前行的途中,会放任自己陷入声色迷障。
她还是由衷地说,“我愿陛下,千秋万岁,心愿得遂。”
皇帝很温和地看着她,彼此目光沉沉而坦然,“你是我最好的伙伴,自此后我的伙伴,都不及你。”
门前的常泰打起密实的毡帘,她退了出去。盥洗梳头的宫人,从她身边走过,鱼贯而入。
赵有良掖着手,就站在门外等她,嘴角笑容的弧度,仿佛都没有改变,“一月不见,姑娘又来了。”
她也笑,“一月不见,谙达风采更胜从前。”
赵有良笑而不语,招了招手,小太监把早已准备好的风灯和伞送过来,连朝一并接过,福保站在一旁,奉命送她出宫。
赵有良摆出明面上的歉然,“姑娘是在养心殿当过差的,知道一天里就数早晨最忙。姑娘回来一趟,我有心想再送送姑娘,实在抽不开身。这不,”赵有良指了指面前的羊角灯,“给姑娘送来一盏最亮的灯,不怕风不怕雪的。福保又是领你来的人,这回也送姑娘,稳稳当当地家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