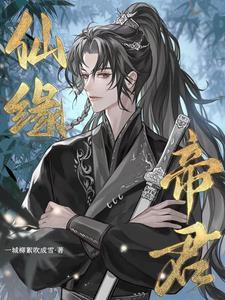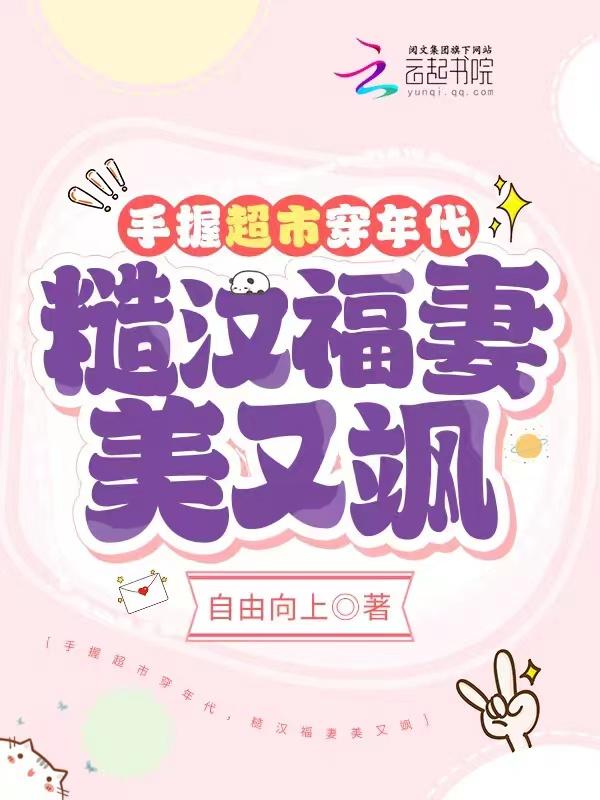紫夜小说>破帷什么意思 > 第98章 纸灰落处起春风(第1页)
第98章 纸灰落处起春风(第1页)
林昭然伸手抹了把眼角,指腹沾了湿意,却没急着擦——那湿痕像是从骨缝里渗出的夜露,黏在皮肤上,迟迟不干。
案头的油灯结了灯花,噼啪炸响,火芯跳动如心跳,将她映在墙上的影子震得晃了晃,像一帧未定格的旧梦。
程知微抱着一摞青布封皮的簿子回来时,她正对着最上面那本《七坊传抄录》怔——墨迹未干的“道在问处”四个字,在纸页间层层叠叠,像春草从石缝里钻出来,这儿一丛,那儿一丛,竟连成了片。
墨香混着陈纸的微霉味扑入鼻腔,她指尖轻抚过字迹边缘,触到一丝微凸的墨痕,仿佛那字正从纸里往外长。
“逾三百人。”她指尖划过“七坊”那栏的总计数字,声音轻得像怕惊着纸页,“三州的私塾……自设了‘问学日’?”程知微把簿子往桌上一摊,竹简串成的书脊出细碎的响,像枯叶在风中摩擦,“不止。今早收的急递,有个叫张二牛的童生,拿竹片刻了这四字,挂在脖子上,说是‘比金贵’。”他搓了搓冻红的手,指节泛白,呵出的白气在灯下凝成薄雾,“可昭然,这势头虽好……”
“虽好,却散。”林昭然替他说完,指节叩了叩案上的典砖。
砖面的刻痕还带着窑温,指尖传来微烫的触感,她想起昨夜在紫宸殿外看到的飞檐,冷铁似的轮廓悬在云里,像把刀——若这三百人、三州风,只停在嘴上念、竹片刻,终有一日会被那刀劈散。
她抬眼看向佛龛后的守拙,老和尚正往铜炉里添香,香条入炉时出极轻的“滋”声,灰烟盘旋着升起来,在他脸上织了层薄纱,烛光透过烟缕,在他皱纹间投下流动的暗影,像被风吹皱的老潭水。
“守拙师父。”她唤了一声。
守拙添香的手顿住,香灰簌簌落在供桌上,像下了场细雪,触地无声,却让空气里多了一丝微颤的静。
“典砖已埋进仪注册,可砖再沉,终是死物。”林昭然起身,襕衫下摆扫过满地砖模,布料摩擦着粗陶边缘,出沙沙的轻响,“我要‘答在天下’四字,不单入眼,更入制。”守拙转过脸,烛火映着他眼角的皱纹,像被风吹皱的老潭水。
他沉默片刻,忽然弯腰钻进佛龛后的暗格,再直起腰时,掌心托着块黑黢黢的陶片。
“前朝‘庶议堂’的议事印模。”他用袖子擦了擦陶片,露出模糊的纹路,陶面粗糙,边缘有裂璺,指尖抚过,能触到岁月啃噬的凹痕,“当年士子议事,盖了这印,才算数。”林昭然接过陶片,指腹触到刻痕里的积尘,一股陈年土腥味钻入鼻腔,突然想起初入国子监那天,缩在最后一排听博士讲“礼者,序也”——那时她连摸一摸刻着“礼”字的石碑都不敢,此刻却捧着前朝遗印,像捧着颗将醒的种子,温热从掌心缓缓渗入血脉。
“程兄。”她转头时,程知微正对着窗外搓手,指节被冻得白,呵气成霜,“吏部那边……”“查着了。”程知微从怀里掏出张皱巴巴的公文,纸面冰凉,边缘卷曲,“礼部尚书现《明堂策》旧驳文被调阅过,沈相三天没批折子。尚书台了密令,说要抓‘伪造辅遗训’的,已经拘了七个传抄的儒生。”他喉结动了动,“我去大牢看了,都是些穷酸秀才,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林昭然的指甲掐进陶片边缘,陶刺扎进皮肉,一丝锐痛让她清醒。
她想起那些在书肆里抄书的人,有的是卖炭的,有的是缝鞋的,抄完了就把纸页往怀里揣,贴着胸口,像揣着块暖手炉——那温度,是信念在皮肉下燃烧。
“可有绣娘被捕?”她突然问。
程知微愣了愣,摇头:“没听说。那些绣娘在织坊做活,官府嫌她们手笨嘴拙,懒得管。”林昭然摸了摸襕衫领衬,那里藏着道暗纹,是柳明漪用“乱针绣”刺的——针脚长短不一,外人看是团乱麻,懂的人一数,就是“问学社”的名录,指尖摩挲时,能感到细微的凸起,像藏在布里的密语。
“他们抓纸,我们织布。”她把陶片往程知微手里一塞,“布上的字,非书非帖,何罪之有?”话音未落,庙门被风撞开,冷风裹着雪粒扑入,吹得油灯剧烈晃动,柳明漪裹着身靛青夹袄挤进来,间沾着碎雪,睫毛上凝着细霜,呵出的气带着清冽的寒香。
她怀里抱着个绣绷,绷上是半幅素缎,针脚细密如星子,银针在灯下闪着微光:“昭然,州府的岁贡缎子这月就要送进宫了,边幅空着三寸——”“绣上‘问学社’名录。”林昭然接过绣绷,指尖抚过未完工的针脚,丝线柔韧,触感如春蚕吐出的初丝,“用你教的‘云纹隐字’,一寸针脚记一个名字。等缎子送到学官案头,他们拆了边幅,自然看得见。”
柳明漪的眼睛亮了,像星子落进深潭。
她从袖里摸出根银簪,在绷上划了道线:“我这就去联络各坊绣娘,三日后准能完工。”话音未落,人已旋出庙门,靛青夹袄扫过满地砖模,带起一阵风,把程知微的公文吹得哗哗响,纸页翻飞如受惊的鸟。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同一轮月光,此时正斜照进沈府西花厅的雕窗,落在沈砚之眉间那道深纹上。
沈府的西花厅里,沈砚之正对着案头的奏报出神。
烛火在他脸上投下阴影,将眉间的川字纹拉得更长了,像一道未解的天问。
“相爷,茶凉了。”孙奉捧着茶盏站在廊下,声音轻得像怕惊着檐角的铜铃,茶面微颤,倒映着跳动的烛光。
沈砚之这才想起自己已坐了大半个时辰,案上的奏报堆成小山,有州官的参劾折子,说“问学社”聚众惑民;也有县令的请命呈文,求复乡校旧制。
他翻开《明堂策》驳文,朱笔悬在“可议”二字上方,迟迟落不下去。
“昨夜宫门守卫截了块绣帕。”孙奉凑近些,压低声音,“是内织坊的女工绣的,上面四个字——‘道在问处’。”沈砚之的手指顿住,朱笔在纸上洇出个墨点,像一滴凝固的血。
“她们说……”孙奉喉结动了动,“说是沈相心里的话。”
心里的话?
沈砚之闭了闭眼。
他想起幼时在族学读书,先生指着“礼”字碑说“这是规矩”,可他望着碑下玩耍的小书童,突然想问“他们为何不能读书”。
这个念头像颗刺,扎了他三十年,此刻却被一方绣帕轻轻挑开。
“织坊女工月俸多少?”他突然问。
孙奉一怔:“三百文,不得识字。”
“三百文。”沈砚之重复着,指节抵着额角,指尖传来太阳穴的搏动,“我守了百年礼法,却不知礼法之外,还有人心。”
庙外的雪不知何时停了。
林昭然站在门槛上,望着东方泛起鱼肚白,晨雾如纱,裹着早市飘来的热粥香气,她却无心留意,只攥着袖中前朝陶印,指节因用力泛白,陶片边缘硌着掌心,痛感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