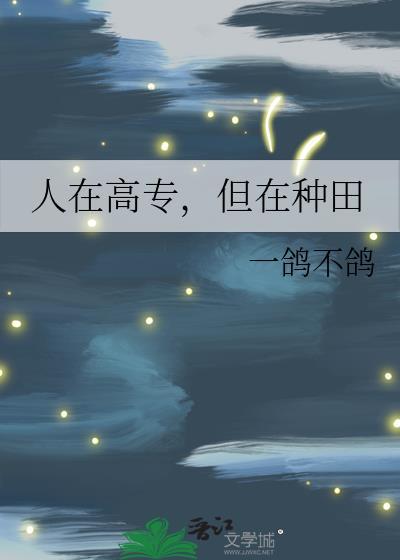紫夜小说>在爱里的我 > 第308封 青衿载梦越千年(第4页)
第308封 青衿载梦越千年(第4页)
技术员小周的电脑屏幕泛着冷光,屏幕上的《农政全书》里ar模型里,徐光启刚弯下腰,指尖悬在虚拟的农具上方——
他正调试“演示插秧角度”的交互节点,连呼吸都放轻了,怕惊扰了这跨越四百年的“教学”。
策划案摊在键盘边,“联动农业品牌做‘古法种植’推广”的标题旁,他画了一个小小的稻穗,笔尖的墨还没干透。
我坐在靠窗的木桌前,台灯的光晕,刚好罩住摊开的《天工开物》。
指尖拂过“乃粒”篇泛黄的纸页,墨字里藏着的稻作技巧正一点点浮出来:
“浸种宜用腊水”、“秧生三十日即拔起”……这些带着草木气息的字句,恰好能接住有机米品牌递来的橄榄枝。
他们要在包装上,印上古人的智慧,让每袋米都带着一点“从古籍里长出来”的分量。
窗外的月光漫进来,落在小周敲击键盘的指节上,也落在我手边的宣纸上。
刚抄录的“稻宜晚”三个字,笔锋还带着墨的润意。
打印机突然吐出新的设计稿,上面是《天工开物》的版画与现代稻田的拼贴。
油墨的香混着桌上冷掉的茶气,在空气里漫出一种奇妙的黏稠感,像把旧时光的碎片,一点点粘进了当下的日子里。
小周突然回头,眼里带着熬夜的红血丝:
“锦姐,你看这段ar动画,徐光启的袖子会不会太飘了?”
我凑过去时,屏幕里的古人正转身,衣袂扫过虚拟的稻穗,光影晃动间,竟分不清是他走进了现代,还是我们掉进了那本黄的书里。
后半夜的风从窗缝钻进来,吹得台灯的光晕晃了晃。
我看着墙上“进度o”的便签,突然觉得这亮到天明的灯,其实是在给那些沉睡的古籍当引路灯——
让它们从书架上走下来,走到稻田里,走到米袋上,走到更多人伸手就能摸到的地方。
上周,去商场看投放效果,大屏正循环播放《蚕织图》的ar动画——
缫丝的农妇指尖缠着莹白的丝线,织机的木梭在屏幕上“咻咻”穿梭,连蚕丝从蚕茧到面料的每一步,都看得清清楚楚。
人群里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举着手机怼到屏幕前,镜头追着动画里的“蚕宝宝”转,辫梢的红绸带随着动作一甩一甩。
她妈妈站在旁边,看着屏幕里蚕丝变成绸缎的过程,忽然笑着摸了摸女儿的头:
“你看,妈妈那条真丝裙子,最早就是这么一点点织出来的呢,比动画片里的故事还神奇。”
小姑娘歪着头看了会儿,突然拽着妈妈的手往女装区跑:
“那我们去看看裙子上,有没有小蚕宝宝的脚印!”
刚想着这画面,手机就震了震,是李总来的消息:
“地铁屏广告加投十个城市,方案你盯一下,下周就要上。”
屏幕亮着,映得我手心有点暖。
原来,那些藏在古籍里的手艺,真能顺着光,走到人潮里去。
窗外的天快亮了,晨光正顺着老樟木书架爬上来,照在你趴在桌上画的分镜稿上。
那上面,《考工记》里的匠人正拿着凿子,在现代建筑的玻璃幕墙上,刻下传统纹样的光影。
我突然想起,你说的那句话:
“创业,哪是赶路,是带着老物件找新家。”
如今再看,那些蒙尘的古籍似在微光里舒展页脚,冰冷的屏幕也染上了指尖的温度,而我们熬红的眼,映着同一束光——都在为让传统活在当下而使劲。
古籍不再是束之高阁的沉默者,屏幕也不是隔绝人心的壁垒,连我们眼里的红血丝,都像是为这桩心事跳动的星火。
大家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力,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前人的智慧借我们的手传下去,当下的巧思又为古老的故事添了新注脚,多好。
砚台里的墨汁,凝着一层青碧色的光,是你昨天傍晚特意磨的。
当时你边转着墨锭边说:
“新笔得用陈墨养,就像好胚子得经慢火煨,急不得。”
笔架上那支狼毫,果然润得亮,笔锋垂着,像蓄着一汪待的墨。
茶缸底沉着半盏凉透的茶,叶底蜷着没舒展透。我去茶具上续壶热的来,紫砂壶里的祁门红正沸着,冲开时该能漫出一些蜜香。
等会儿,跟印刷厂对古籍复刻版的广告插页,得盯紧了——
你总说“墨色不能抢了纸香”,那些泛黄的纸页里藏着的旧时光,得让看的人先闻见草木气,再瞧见笔墨痕。
对了,你搁冰箱里的绿豆汤,我撒了一把陈皮进去。
瓷勺舀起来时,该能尝到一点清苦里的回甘,配着这秋老虎天正好。
明天去布庄量尺寸,别忘了带上那把老铜尺。
上次,你摩挲着尺上的刻痕说“这是光绪年的活儿”,我倒想试试,它能不能量出,从那时到现在,时光到底走了多远的路。
喜欢在爱里刻下年轮请大家收藏:dududu在爱里刻下年轮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