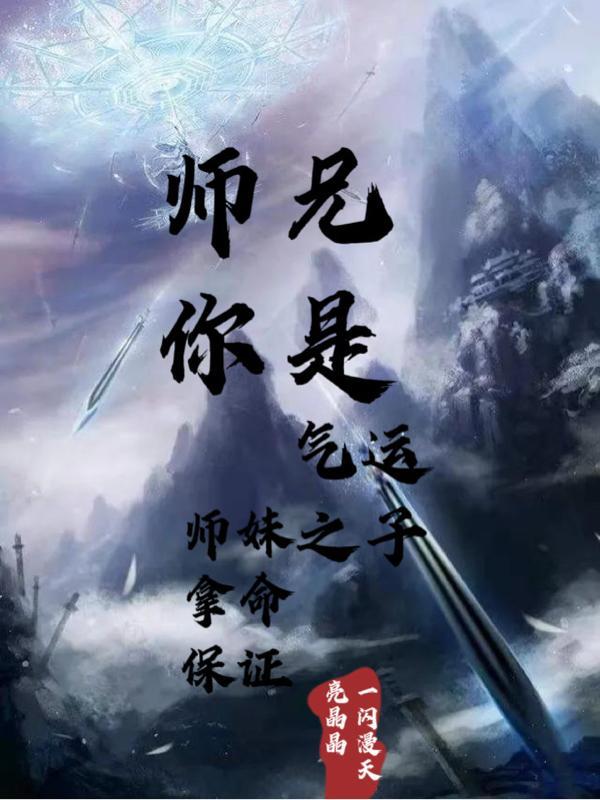紫夜小说>穿成团宠小公主[古穿今 > 第101章 船载浮坝入江南(第1页)
第101章 船载浮坝入江南(第1页)
楚知夏带着工匠和兵丁登船那天,江南的雨下得邪乎,跟老天爷撕破了口袋似的,直往下倒。
码头跳板被雨水泡得溜滑,有个兵丁扛着楠竹没踩稳,“噗通”摔进水里,溅起的泥点子糊了楚知夏半张脸。
“小心点!”她抹了把脸,把湿透的鬓角别到耳后,“这竹子可是咱的命根子,摔断了咱都得在水里泡着!”
船舷边堆着的楠竹,足有碗口粗,码得跟小山似的,竹节上还挂着新鲜的竹叶,被雨水打得蔫头耷脑。
后舱更热闹,浸过沥青的羊皮囊,鼓鼓囊囊码了半舱,黑亮亮的油光顺着囊子往下滴,把舱板浸得油乎乎的。
威廉抱着他那卷威尼斯防水布,在摇晃的船舱里东倒西歪,卷上的水珠甩得跟下雨似的:“公主,威尼斯的水从来温文尔雅,哪像这样撒野!”
楚知夏正弯腰检查绑竹排的麻绳,听威廉这么一说,直起腰笑了起来:“它这是给咱来个下马威呢。”
她扒着船帮往岸边瞅,浑浊的浪头跟疯了似的拍着船板,“咚咚”响得像敲鼓。
岸边的老柳树半截泡在水里,树干上的青苔被冲得干干净净,可树梢的新枝照样往上蹿,绿得亮。
“你看那柳树,根在水里泡了半个月,枝子该长还长——这就叫韧性,咱的浮坝就得学这个。硬邦邦的跟水对着干,迟早得被冲垮,顺着它的劲儿来,才能治住它。”
船队刚过淮河,天擦黑时就瞧见沿岸的高坡上挤满了逃荒的百姓。
草棚子搭得东倒西歪,破被单在雨里飘得像面烂旗子。
有个老婆婆,怀里抱着个瘦得只剩皮包骨的孩子,举着半块霉的窝头往船边凑,浑浊的眼泪混着雨水往下淌:“官爷,行行好……给口吃的吧,俺孙子三天没沾粮食了,眼瞅着就快不行了……”
楚知夏心里一揪,扭头冲兵丁喊:“把船上的干粮分一半给百姓!”
“公主,那是咱的口粮啊!”
管后勤的小吏急得直跺脚,“到了江南还不知啥情况,咱自己都得省着吃!”
“咱少吃两口饿不死,他们再不吃就得真没了。”
楚知夏蹲下身,把老婆婆手里的霉窝头,掰下来一小块,往自己嘴里塞。
又苦又涩的味道直呛嗓子,她强咽下去,指着远处的水洼说:“您看那水洼里的鱼,抢食的时候都知道让着点同伴,咱活人还能不如鱼?”
她让兵丁把干粮袋子解开,自己亲手往百姓手里递饼子,“大伙儿再忍忍,等水退了,咱把田种起来,不愁没饭吃。”
蹲在草棚子底下避雨时,楚知夏借着马灯的光看地形。
地上的烂泥被她划出一道道沟:“你看这河道,拐得跟咱工坊里的曲轴似的,水流到这儿就得打个旋。先前的堤坝愣在这儿硬堵,水越涨越急,可不就把堤岸冲垮了?”
她在泥地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竹排,“咱先在支流试试水,用竹排扎三里长的浮坝,让水有处泄,别一股脑全往主河道挤。就像给堵住的水管开个小口,压力小了,自然就不崩了。”
话音刚落,就见几个穿着蓑衣的汉子,踩着泥水过来,领头的张老汉六十来岁,胡子上挂着泥疙瘩,手里的长烟杆往地上一磕,“啪”地溅起串泥点:“公主殿下,不是老汉多嘴,治水得靠土堤扎根基,那才叫稳当。您这竹排漂在水上,风一吹就歪,不是拿百姓性命开玩笑?”
楚知夏没起身,指着远处被冲垮的堤岸,那地方还在往下淌泥水,断口处的石头被冲得七零八落。
“张老爹,您看那土堤,石头垒得够结实吧?现在不也成了烂泥?”
她拍了拍身边的楠竹,竹身硬得能硌手,“咱各干各的试试?您带徒弟修土堤,我领着人扎浮坝,三天后看谁的能挡住水。要是我的法子不行,我给您端茶认错;要是成了,您就帮我搭把手,咋样?”
张老汉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在雨里明明灭灭。
他瞅着楚知夏那双沾着泥的布鞋,又看了看远处哭哭啼啼的百姓,闷了半天吐出句:“行,就依你。但要是出了岔子,老汉头一个不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