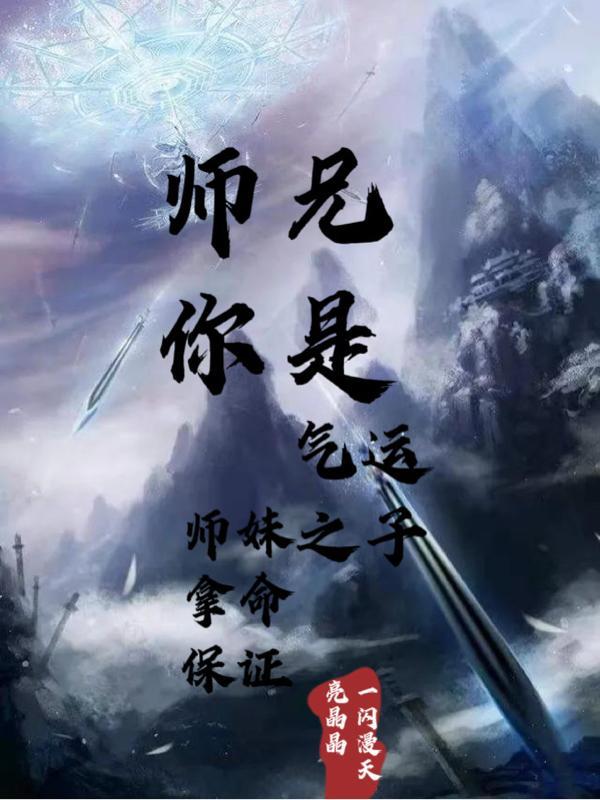紫夜小说>丫鬟主母不好惹 > 第83章 初遇管家暗藏机锋(第1页)
第83章 初遇管家暗藏机锋(第1页)
沈悦睡着了。
她侧躺着,手搭在肚子上,呼吸很轻。屋里没点灯,只有帘子缝里漏进一点光,照在她脚边的地毯上。
书诗站在门边,墨情靠在床尾。两人没说话,一个盯门口,一个盯窗户。
外头脚步响了。
由远到近,停在门外。
“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一条缝。
一个穿青灰袍子的老头探头进来。他手里端着个托盘,上面放着碗热汤。
“老奴来给少夫人送安神汤。”他声音不高不低,“刚熬好的,暖胃又助眠。”
书诗没动。
墨情也没应。
老头笑了笑,往前迈半步:“主子歇下了?那我轻点放桌上。”
他说着就要往里走。
屏风后头,诗画从暗处走出来。她没戴簪子,头用布条绑着,手里捏着本账册。
“放下吧。”她说,“我们自己来。”
老头一愣,转头看她。
“你是?”
“掌账的。”诗画站到桌前,“我家主子的东西,不劳外人经手。”
老头脸上的笑淡了些。他把托盘搁在门边小几上,没退。
“也是,新妇进门,身边得有贴心人。”他说,“不过王府规矩,各院饮食由厨房统管,这汤……若凉了不好。”
诗画翻开账册,头也不抬:“我们带了私灶,从明日起三餐自理。”
老头眉毛动了下:“私灶?可报了名册?领了火牌?”
“户部批文在我这儿。”诗画翻一页,“陪嫁物产独立记账,采买自办,不入府库,不沾公账。条文第十七条写得清楚。”
老头不笑了。
他看了眼紫檀木箱,又扫了眼案几上的文书。
“那……嫁妆呢?”他问,“可归了档?入了册?要不要这边帮着清点?省得出错。”
诗画合上账册,抬眼看他:“你管过几回新妇嫁妆?”
“十多年了。”老头说,“左相府、礼部尚书家都经手过。”
“那你知道,嫁妆箱钥匙只有一把。”诗画说,“在我主子手里。谁碰,就是犯法。”
老头眼神闪了闪。
“我不是要碰。”他说,“就是问问安置的地方。万一失窃,咱们都担不起。”
诗画走近一步:“箱子昨晚就锁好了。账本也封了。你要查,去户部调令状。要报备,找工部领文书。在这问我,没用。”
老头站着不动。
屋里静下来。
外头风刮了一下窗棂。
诗画没退。
她就站在桌边,手搭在账册上,像根钉子。
老头终于笑了下,这次是冷笑。
“姑娘好本事。”他说,“难怪一进门就换香换茶,连床都不让人近。”
诗画不接话。
“你们主子……真不管事?”老头看着软榻方向,“整日歇着,也不认人,不理事?”
“她累了。”诗画说,“你想让她什么时候醒?”
“不是我想。”老头压低声音,“是有人想知道,这位少夫人,到底是装傻,还是真懒。”
诗画嘴角动了下。
“她爱吃,爱睡,不爱争。”她说,“可要是谁想占她便宜,偷她东西,害她性命——”
她顿了顿。
“我们四个,一个都不少。”
老头盯着她看了几秒。
然后转身往外走。